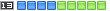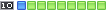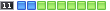尹姨去世有三四年了吧。她生前是妈妈的朋友。她的老家和妈妈的老家是临县。她,一个普通不过的女人,在我的心里,却总有着她的位置。我的脑海里,过去的事象浪一样涌来之时,浪花翻起的地方,就有她的那张脸,一种谈谈的怀念,萦绕着我的心。
从记事起,我就认识她了。爸爸工作的电影厂,有不少男人娶的是老家的女人做老婆。尹姨的丈夫,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老实,小个子,相貌端正。尹姨就是所谓单位家属。他们和我们不住在一个宿舍。离我家也就走十分钟的路的样子。六十年代初,街道办了一些工厂,不少妈妈和尹姨这样的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作。尹姨和我妈妈,同在一个服装厂,当时叫“缝纫厂”的。妈妈是管人保的干部。尹姨是个普通工人。
尹姨和他丈夫,好像是包办的婚姻,她大她丈夫两三岁。但看上去大很多。对她的记忆,从开始的样子,她就像一个老太婆,一口老家话,穿得土里土气,头发稀少,高颧骨,瘪嘴,满脸皱纹。到她七老八十的时候,她的脸也没有怎么变。人家叫她老尹,我妈也叫她老尹。有人说她长得象黄世仁他妈。
小时候,我上厂里托儿所。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有时我妈忙,尹姨就接我到她家里。给我吃喝,还让她的女儿们陪我玩,在她家过过夜。她有一个女儿大我一两岁,一个儿子跟我一般大,一个女儿小我一两岁,长得都不像她,个个灵眉大眼地端正好看。她做的饭,我吃得香甜。没记得在她家有过好吃的。只是是咸菜稀粥,就烙饼或馒头。那粥稀得,就比米汤稠一点。妈妈熬粥,总是放米太多。爸爸总说那不是粥,老尹家的粥才象粥。尹姨对我是真心地好。待我小公主似地,好像我特别金贵。年复一年地呆在托儿所里,老师阿姨个个冷漠。孩子们也多是以强欺弱。孤独的我,谁对我好,心里记得。
文革来了。我爸爸被揪出来批斗了。斗够了,就蹲牛棚。不久,我妈也被揪斗。先是被游街,游街之后造反派就顺便把她送到北京第二监狱去了。监狱的人不敢不收。我妈妈就稀里糊涂地被关了六个多月。等到出来以后,她厂里的三几个姐妹,就来家里看她。老尹阿姨就在其中,她想法安慰妈妈,问寒问暖,端茶倒水又扫地。看得出,她很看重妈妈。看重得有些崇拜的意味。她自己,似乎永远是个陪衬,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或许,同是一样的农村背景,妈妈就学了文化?或许,妈妈嫁得地位高一点?或许,妈妈是厂里的干部?不得而知。一个女人,一生都是仰望着别人活着,也许从来也没有看到她自己,其实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
因为运动,妈妈失去了以前的一些好朋友。有的人可能怕被牵连。有的人可能是诚心划清界限。但尹姨不怕,她对妈妈崇拜,对我好从来没有变过。其实她根本就不会被牵连,她是个富农分子。妈妈说,老尹从小就下地干活,一直是被家里当做壮劳力使唤的。可是,土改那年,她十八岁。因为家里有地,够上富农的标准,她又够了年纪,于是,就戴上了一顶富农的帽子。好在她丈夫的家里是贫农。搞运动,没有怎么触及到她。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话都说不清楚,别人也懒得去理。但是,这个富农的帽子,在后来的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帮她摘下来。
富农的事,可能是尹姨的一块心病。人们一批批地被打倒,又一批批地被平反。后来妈妈就被平反了,还当上了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可尹姨的富农分子帽子,却是恒久不变地戴着。她就来找妈妈,跟她念叨。一来二去地,妈妈就烦了。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十三、四岁吧。一个小学生,已经负责家里买菜做饭的事了。那天,我正在揉面要蒸馒头。妈妈刚下班,尹姨后脚就进来了。我妈这个人,可能做姑娘时候下地种田,所以不擅长做饭。我从邻居的阿姨那里,学会了发面,使碱,蒸馒头。刚学会,就兴趣很浓,这几天吃了好几次馒头。妈妈见到尹姨进门,眉头就皱起来了,对她代答不理地,只问我晚饭吃什么,怎么还没有做完。我回答说吃馒头。妈妈立即火了,对我大声斥责起来。说昨天才吃了馒头,今天又吃馒头。我不敢出声。尹姨看我妈发火,也吓得够呛,连忙又劝又哄。一边帮我揉面做馒头,一边帮我说好话。妈妈气未消,还是一个劲地骂我。我感觉得到她的生气有些过分,可能是看到尹姨来,很不高兴的缘故。心里对自己挨骂感到委屈,也为尹姨感到不平。为什么不喜欢她来。看到尹姨来,我怎么就感到高兴呢?但看到妈妈对尹姨抱怨我,又有些怀疑真是生我气。又不敢说话,只有默默地跟着两个大人把饭做好。妈妈吃着饭,气消了。尹姨跟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她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妈妈发火是跟她有关。看到家里平静了。她就回家了。她走后,妈妈带有歉意地说,她发火不是因为又吃馒头,是看到老尹又来了,嫌她烦。
到现在,我还是有些不理解妈妈。我的朋友来找我,我会觉得被人家瞧得起,会高兴。除了有极端自私的人,来找你只是为了有所求,或是炫耀自己或是倒垃圾地唠叨,我会烦。对我好的人,我会感激,即使有些说话啰嗦语言枯燥,我也会包涵的。妈妈对尹姨的冷淡,可能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关系很近,不缺少人情。不像我们现在,找到对自己好的人,又是无条件地好的人,不容易。
妈妈也许对尹姨说话常常有不耐烦的时候,但她还是给她面子的。尹姨的丈夫,却常常是没有好气,没有好脸。尹姨习惯了。
唐山地震厂里新盖了宿舍楼,尹姨跟我们住前后楼。我后来上大学,又出了国。妈妈退休,爸爸病故。妈妈一个人在北京的家里生活。闷的时候,几个过去的邻居兼朋友又凑在一起,聊聊天,打麻将,玩扑克牌。尹姨又跟妈妈经常来往了。
那年第一次带着孩子们回国。尹姨见到我的有外国人血统的孩子们,稀罕得什么似的。一天跑我们家好几次,嘴里总是念叨着:不知道孩子们喜欢吃什么?孩子们吃什么好?好像这个问题,把她实在给难住了。大早晨起来,门铃就响了。是尹姨,带来了从市场上买来的新鲜蔬菜。妈妈就说:你怎么又买菜了,昨天你买来的那些,还没有吃呢?原来尹姨每天早晨很早就起身了,蹬上一个平板三轮车就出去买菜了。等她买回来,人们才刚刚起身。尹姨坐在那里,一个劲地盯着孩子们看。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里,喜欢吃什么。我一边让孩子叫姥姥。一边帮他们回答问题。两个女儿被盯得发毛,就用不流利的中文说:“不要姥姥,不要姥姥。”也难怪,周围尽是这样的老太太们,总是这样看他们,问他们些听不懂的问题。
饭摆上桌子,尹姨还没有走,想看看孩子们怎么吃饭吧。一向挑食的大女儿拒绝吃米饭,闹着要吃“饼饼”(烙饼)。我本来不想迁就她。尹姨却好像很感动,唠叨着说,“人家孩子要吃烙饼,这可怎么好?”一边遗憾自己家没有烙饼,就跑到阳台上,大声喊楼下的一个老太太,问他们家有没有烙饼。那边的老太太也被惊动了,出来说家里本来有的,刚吃完了。尹姨就要出去买。我连忙阻止了她,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跑到厨房去烙饼。
有人送了月饼给我们,包装很漂亮。打开来一吃,莲蓉是假的,又甜又腻。孩子们不吃,我不吃,我妈也不吃。尹姨来了。妈妈就让尹姨吃。尹姨一边说扔了可惜,一边就把一整个月饼吃了下去。再给她,她说放着吧,下次来了再吃。
尹姨终于想出了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她带来了几个煮熟的老玉米。孩子们还是不吃,我和我妈吃了好几天才吃完。
家里地方小,就带着孩子们在街上散步,路上见到了尹姨。应她邀请,就带孩子跟着她,去了她家。尹姨高兴得象来了贵宾。
她家的寒碜,出过我的想象。两间小屋的单元,又黑又暗。一间是给孙子住,一间是他们老两口住。一间屋半边是床,陈旧的家具床褥,没有一点温暖舒适的感觉。尹姨的丈夫几年前得了脑血栓。成了半瘫,坐在床上。头发半秃,面部肌肉僵硬,说话不成句,好像有些痴呆。我们困难地交谈。尹姨一边当翻译似地在我们中间插话,又一边找出了点水果让我们吃。喜欢植物的我,注意到房里唯一有生气的东西,是一个瓦盆里种的茉莉花,在北京寒冷萧索的冬天里,绿叶油油地发着一股诱人的生气。我说花长得好。尹姨注意到我在楼外面的时候就对着花园里的花木看了很久,明白我喜欢花草。就拿出了几张照片,上面有她在原来住的地方种的石榴树,她说那棵树一年结一百多个果子。走时她给了我一个大石榴,让我带回澳大利亚种。
在妈妈她们这群老太太里,尹姨年龄最大,身体却最好。她过了八十岁,还是那样地健朗。走路通通响,说话底气足。每天还总是蹬着三轮车出去买菜,帮妈妈代买,帮邻居捎东带西。我妈说照这样,老尹能活过一百岁。我真心希望她活过一百岁。妈妈孤寂的生活,也好有一个热心的,对她好的伴。
一天,几个老太太在我们家打牌,散的时候,两个老太太拖着病病歪歪的身体,用手扶着楼梯栏杆,从三楼慢慢地挨下楼梯。尹姨从后面出来,通通通地下楼,看到这两个老太太这样慢慢地挨,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这么慢,离死不远了吧?两个老太太笑道:你还别说嘴。俗话说,破笊篱熬过柏木勺。兴许你还死在我们前边那。
不出一个星期,尹姨住院了。说是脑子里面长了一个瘤。妈妈她们去看她,她还象平常时候一样,说说笑笑地。说很快就会出院。好像也就一两个月以后,她就走了。去世前的情形,我妈妈没有讲。我想,尹姨那样的人,生时是懵懵懂懂地快乐着的,死时,也应该是懵懵懂懂地快乐着走。
我后来回国,听不见了她那亲切的家乡口音,看不到了她那风风火火的脚步。每次路过她家楼前,就望望那边,指着她家的方向,问孩子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姥姥。
2009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