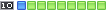一个人的经历,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剪影,一段历史的印记。
在我与苏俄打交道的30多年里,苏俄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昨天有位朋友向我建议,能否写写自己在俄罗斯的亲身经历,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体会,翻译工作的酸甜苦辣,生活在俄罗斯的喜怒哀乐。朋友的建议很好,所以在以后的文章里,我将记录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由此新的系列定名为《俄罗斯笔记》——题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刚刚结束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处在冰点。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词。刚刚出道担任翻译工作的我,被领导反复告知,在和苏联人的接触交往中,要始终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丝毫不能麻痹大意,要坚决地彻底地毫不迟疑地和苏修作斗争。因此在那个时期突出一个斗字。
在和苏联人的接触中,有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克格勃",一提到它,人们的心里就会蒙上一抹阴影。
克格勃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缩写是КГБ,按字母发音读成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是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后改成内务部,但人们习惯上仍称之为克格勃。
在克格勃的历史上,有四个值得一提的人物。第一个是捷尔任斯基,他也是肃反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是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得力助手,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第二个是贝利亚,他是斯大林的左臂右膀。斯大林死后,被判为祖国的叛徒,人民的敌人,被处决.
第三个是颇有儒将风度的安德罗波夫,他是勃列日涅夫的重要搭挡,勃氏死后,出掌克里姆林宫帅印,未及几时病死.
第四个是普京,叶利钦执政时的内务部长,叶利钦辞职后接任俄罗斯总统。
人们之所以对克格勃心存阴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为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扩大化推波助澜,滥杀了许多无辜。
1993年我在远东边陲重镇伊尔库茨克市看到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遗迹。距伊尔库茨克国际机场跑道端不远,有一片小松林,松林的入口处树立着一块木牌,上面有一行醒目的文字: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走进松林,有三个墓穴,分别编为1,2,3号墓.一号墓长8米,宽6米,深6米;2,、3号墓长6米,宽5米,深6米。墓地周围散落着尚未腐烂的皮靴、眼镜、铝制饭盒、酒壶。陪同我参观的东西伯利亚民航局长告诉我,这是当年肃反时造成的悲剧,从三个墓穴的容量看,被处死的有万人以上。在纪念墙上标着能查实的人员姓名,死者的职业都是工人、教员、技师、司机、工程师、医生、护士------其中到底有多少"反革命",只有上帝知道.
由此,多少年来,克格勃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听. 克格勃,说白了就是特务间谍机构,其职能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 前苏联克格勃的总部大楼位于莫斯科的捷尔任斯基广场,广场中央是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雕像。这座灰色的大楼始终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苏联人把这座大楼比喻成一张覆盖全球的硕大无朋的间谍蜘蛛网中心的蜘蛛,其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只知道被国际媒体曝光的若干起重大苏联间谍案,都是在这座大楼里一手策划操纵,但是其中扑朔迷离的内幕仍然不为人知。直到七八十年代,一些前苏联间谍逃往西方后撰写了回忆录,才使世人多多少少了解到克格勃的些许内幕。 克格勃的主要使命就是动用一切手段窃取各国、尤其是敌对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克里姆林宫提供外交政策的决策依据。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以各种身份、各种职业为掩护,活跃在世界各地。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和苏联人的接触交往中特别谨慎小心,不能接受任何私人馈赠的礼物,不能有任何私人之间的接触交往。那时苏联专家都住在使馆,我们去接他们工作时,一般等候在距大门20米以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京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本《色情间谍》。在间谍战中,最能奏效的往往是色情间谍,也就是说使用美人计。前克格勃培养了一大批色情间谍,所选的对象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小伙。按照克格勃的术语,女的称为燕子,男的称为乌鸦。这些燕子乌鸦飞翔在苏联各个角落乃至世界各地,使许多被克格勃猎取的目标对象中箭落马。所以在那个时期,去苏联出差,最害怕的是克格勃对你采取手段,使用美人计。
1980年金秋,我到莫斯科出差。一到使馆招待所,立即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墙上贴着“莫谈国事”、“严守机密”的告示。招待所工作人员要我们拉上窗帘,不要高声谈笑。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前不久刚刚发生了“王XX事件”。使馆商务处反复提醒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不得单独外出; 护照必须随身携带; 不得在旅馆和公开场合谈论不该谈的话题; 住旅馆必须两人一间。
然而哪壶不开提哪壶,越是害怕的事越是要发生。
在使馆休整两天后,我们一行15人坐火车从莫斯科去基辅,按人数是7个半包厢(苏联的软卧包厢是两人一间),其中一人肯定要和苏联人结伴。我们十五人谁也不愿意和毛子哥结伴。没准儿克格勃会设下什么圈套?最后领队决定我和毛子哥结伴,理由是我是翻译,懂俄语。我不干,理由是正因为我是翻译,懂俄语,才不能去。但是领队下了命令我只得服从,我刚走进包厢,吓得立即退了出来。你猜怎么着,那包厢里正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我的脑子里马上冒出“她是不是燕子”的问号。我向领队请求我绝对不能进去,换个人去。领队也为难了。正在为难之际,我想到了陪同我们前往基辅的一位苏联航空出口公司的官员,请他帮忙。他一听乐了,这算啥事,我跟你换个地儿不就行了。现在看来这实在不是问题,可是在那“反修防修”的非常年月,真要有点儿什么事,那可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这种处处提防的紧张心理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以后才慢慢消除。
[em34][em34][em34][em34][em34][em34][em34][em34][em34][em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