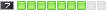“鲁迅精神”审视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肯定鲁迅的是瞿秋白,瞿秋白认为鲁迅是左翼政党的“同路人”,他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认为鲁迅辛辣刻薄的文章是对抗当局的投枪和匕首,特别是鲁迅无情地抨击上世纪二三十代的上海文坛,尽是些“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等等厉语,真有点振聋发聩之感,还有就是看中了“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无法直面的人生——二十年代晚期的鲁迅思想》,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虽然鲁迅曾一度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却始终没有主导和参与左联的工作,也不加入共产党阵营,反是与共产党人周扬等闹翻,他不想受人控制,也不想成为他人手中的政治棋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3份电报,电文称鲁迅为“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同时,在延安创办鲁迅艺术剧院、鲁迅师范学校和鲁迅图书馆。
从1937年到1942年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成功地塑造了延安的鲁迅形象,并使之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延安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符号。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称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他“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演说中着重提出了“鲁迅精神”,总结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最后总结道:“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冠以鲁迅“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头衔;肯定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从此鲁迅的形象被塑造得光明伟岸,不由自主地登上了政治舞台,“鲁迅精神”成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或缺的标杆。
毛泽东是政治家,“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其思维和作为的最高原则,因人、因事、因时、因地来解说同一件事就是政治的需要了。“鲁迅精神”实则是政治家的一个手段、一个口号,其目的性可想而知了,那么“鲁迅精神”的准确和真实性也可想而知了。
1949年至1965年,鲁迅杂文被大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达三十多篇(不包括别人写鲁迅的)。有《少年闰土》、《风波》、《鸭的喜剧》、《兔和猫》、《秋夜》、《一件小事》、《故乡》、《社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药》、《〈呐喊〉自序》、《祝福》、《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论雷峰塔的倒掉》、《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铸剑》、《三月的租界》、《拿来主义》、《狂人日记》、《阿Q正传》、《范爱农》、《藤野先生》、《雪》、《阿长与山海经》、《鲁迅自传》、《灯下漫笔》节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友邦惊诧”论》等等;“文革”中后期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唯一的文学教材。所以周作人说“鲁迅是被政治的原因硬给捧起来了。”
所以要真正的认识鲁迅,就必须摆脱“完人、全人、伟人”的窠臼,才能正确认识他;学习“鲁迅精神”,就必须摆脱政治的束缚,我们才能准确认识鲁迅和“鲁迅精神”,并接受承继他的学问和品格。
鲁迅是永远对“现状”不满的人,是永远挑战权力和权威的人,他注定不会受到任何当权政党欢迎。有段记载说斯诺问鲁迅“阿Q没有犯什么罪,为何被处死”?鲁迅答:“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奴隶的奴隶了。”斯诺又问:“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冯雪峰在回忆录中写道:鲁迅读到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后说毛有“山大王”气,像《水浒传》里占山为王的寨主,然后调侃地问冯雪峰:“你们打来以后,会首先杀我吧?”
鲁迅不相信一切权威和权力者,也不相信社会制度和秩序。鲁迅的意识里始终认为谁取代了上届的统治者,自己就沦为新的统治者,都不是好的!鲁迅天生对一切权力者有深刻的认识,他不相信革命者宣传的“黄金世界”,1925年3月1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写到:“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毛泽东是深知鲁迅性格的,1957年7月7日晚,在中央召开的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问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延锴秘书罗稷南(原名陈小航):“你现在怎么样啊?”罗致谢后小心问:“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件事鲁迅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有披露,与会的黄宗英也撰文给予了佐证。事实上,鲁迅一生从不支持或否定某个政党、某个流派,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学等, 他虽参加, 却总投以怀疑的眼光。不断的怀疑,不断地渲染坚持自己的别样的独到见解,不停的给当权者找麻烦。这就是鲁迅的性格,天下大定,坐牢是他唯一的归宿,早死是鲁迅之大幸!
鲁迅并不讳言自己的偏激,鲁迅在《两地书》中数次自我检讨道: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而我们几十年来却将鲁迅的偏激渲染成最坚定的革命性,对鲁迅的自我批评要么是避而不谈,谈也是牵强附会地从另一种革命的角度来诠释,以至鲁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和“一个都不宽恕”的人生态度成为革命的试金石、分水岭,其直接影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体中国人,成为造反者的“专政武器”。
钱理群《青春是可怕的》一文记录了触目惊心的一幕:“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14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这个悲惨的事实,深刻体现出“痛打落水狗”话语中所潜藏的阴狠暴虐气息!那围绕着池边狂嚷“痛打落水狗”的青少年学生们,不正是在“鲁迅精神”教导下成长的吗?这种冷酷和悲惨的历史现象,不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吗?该学什么、该摒弃什么难道还不清楚了么。
鲁迅偏激,笔走偏锋,把话说死,说得绝对,说到头。比如“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突然想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些话对社会、对青年只能是误导,而不能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给许寿裳信中写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怪哉,《资治通鉴》记载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中国的的史实,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的实例,以作历史的借鉴。其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之绝笔。鲁迅的这种感觉和评判,是绝无仅有的。鲁迅是在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书籍中成长为学者、教授、名家的,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不可取,普通人讲讲影响也许不大,而作为声名遍天下的名人这样宣讲其影响足以引导当代的青年厌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要说得那么绝对、那么过激啊!如果悉心教导青年,指出“中国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劣、可取和该摒弃的,细致、全面、具体、辩证的分析论证,以他的学识当使我们受益无穷啊。名人的偏激,加上过度的政治化就使无数求知的青年“误入歧途”,真的误人子弟了。
《陈旧人物》(叶兆言)书中一件小事证实了鲁迅的敏感和偏激:“鲁迅的倔有时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他到了北京,碰到胡适,胡开玩笑说他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立刻翻脸,说我马上卷土而去。”鲁迅偏激的性格使他看待社会问题总是从最负面论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偶感》)。难怪梁实秋说:“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梁启超则不同,他一针见血地道出社会病根,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讨专制政体檄》)“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候门,三辑三让,以行迎宾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誰指出了社会弊端,谁为社会开出了病方,一目了然了,这是作为“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十分不足的地方。
是啊,胡适先生说的好:“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寻求真理,坚持真理,唤起民众,为真理而奋斗,必然能开创和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
在鲁迅的杂文中屡屡能读到他诋毁他人人格的言辞,他曾称胡适、罗隆基等人向当局争取人格独立的行为是“奴才”对“主子”祈求,以“正人君子”一词调侃砭斥;论战时骂对方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媚态的猫”、“洋场恶少”等等;称共产党员周扬为“奴隶总管”、“横暴者”,将周扬等人视为更可怕的敌人。这些都显现出他性格上的偏激。无怪乎林语堂称鲁迅是“令人担忧的白象”,因为他太特别了,特别得令人担忧。
鲁迅始终没能摆脱中国失意文人的愤世嫉俗,成为一“狂狷”,他没有积极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将怨恨、愤怒和反抗用玩世不恭的言辞来表达出来。故有人明确提出“少不读鲁迅”,因为他刻薄的词语,苍凉的情感会让人颓废而绝望。正是性格和思想上的偏激,鲁迅一生少有乐气,心情常常沉郁、狂躁,拼命抽烟喝酒,不修边幅、囚发蓝衫,习惯于孤独荒漠和冰刀雪剑,以致三十岁便苍老如五六十岁一般,以至五十五岁离开人世。
究竟该学习鲁迅什么呢?
1903年至1908年间,鲁迅发表论文,提出“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鲁迅说“拿苛刻的眼光挑剔自己,用宽容的胸怀对待他人。”后来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在《学界三魂》中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如果鲁迅后来一直秉承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写下去,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影响会更巨大,不是比过激的嘻骂释放更多的正能量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