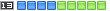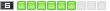我在三管处干了三年
中学毕业就失业一年后,我收到党发来的通知,让我到西安市三管处报到上班。以为是到管天管地管人的地方去干活,结果去了才知道,“三管处”既管天地人,也管“三观”,而是西安市三轮车管理处,也就是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三轮车行业人员全管。
解放前,“站起“前,中国人大多都弯着(在地里干活),蹲着(陕西人最爱的姿势,或是躬着(比如蹬三轮车”上坡崛沟(就是屁股),下坡挺肚)。解放后,旧天变新天,还是得干活挣钱养家糊口。
当年一首歌把人的血脉唱得很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一遍,更使劲)”,直接跟《国际歌》对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没有就没有”,难道不是说共产党就是中国的救世主吗?三皇五帝到如今,唐宋元明清国共。换个朝,被唱成换了个新。新天新朝新太阳。“长鞭A啪啪的响A,沿社会主义奔远方A。咿呀嘿A“。全是虚词,社会主义,远方。
三管处是个“大集体”单位。解放后,东西南北中,吃喝拉撒睡,党是第一位。党出面把三轮车行业组织起来,是人都得听党总支指挥。
好像解放以前三轮车全是真人真蹬,解放二十多年后,三轮车在西安已经机动了。当时西安火车站就有三轮机动车,接南来北往的客。一个司机两个客,一辆三轮摩托车,上边弄个铁棚,下边有个底盘。当年西安人都亲切地把那三轮机动车叫“屎巴牛”,满西安跑的都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一九七五年,新中国二十六年。
我们一进单位,先集中办一周还是两周“学习班“,跟双规差不多。不准回家,反正谁家也没电话。八十多个男生被安排住在一个大车间的厂房。因为五月,不冷。”八月的桂花香又香“,五月的太阳红又红。文革的第九个年头,领导说大话说屁话说废话早就炉火纯青。晚上,大家乱作一团,都是些十八九的小汉子,住的比猪都密,但比猪快乐得多。大家在一起不妄议中央,也不聊女人。因为中央那会就是一个人。女人是不是老虎,我们都不知道。那会都聊些什么呢?反正大家晚上两个多钟头,都很快乐。打牌,输了脑袋上顶砖头。下棋。在大通铺上”演习追击“。
一周两周学习班,一阵风就过去了。大家都是散勇,突然有了组织,相互亲近的紧。三管处下辖三个单位:货运机动车队,客运机动车队,机动车辆修造厂。货运就是东风三轮机动车拉货送货,载重大约一吨。上边是铁皮棚,旁边是帆布包,挡风遮雨窜地虎,西安街上到处有。客运就是西安火车站的“屎巴牛”队,接客拉客很繁忙,人民坐上机动车。车照样是东风三轮车,喷漆铁皮全包,不能让客人淋着。坐在里头很憋,当恋人特别喜欢。机动车辆制造厂,叫夸张了,对外说是造东风机动三轮车,当年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到处东风。大多数人都想去车队,因为车队不学徒,考了执照就可以“多劳多得”了。那些年头,人想也是白想,白想人人都想,想清楚了听从党招唤。我因为无知,不光是无畏,也不白想,爱谁谁,党给口饭吃就吃一口。愉快,全是因为年轻。脑子,嘴巴全是多余,但力气跟泉水一样。
我分到了机动车辆修造厂,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人去了车队。说是修造厂,实际上是装配厂,引擎是买的,底盘骨架还有些玩意是自己翻砂自己造。有些东西要煅,就是打铁。师傅小锤一点,你就得抡起十八磅的大铁锤砸。铁块熊熊,火光四射,锤起骨松,锤下汗出。我打过些日子,真TM累。车壳子也是自造,用最多的是0.75毫米的铁皮,什么驾驶盘,窗子框,车前脸,小车门,都是小木锤一下一下敲出来的。这活叫钣金,是技术活。修壶砸铁簸箕做哈米管都是钣金。林海雪原里的滦平,是前辈。还有的工种是喷漆,敲出来的东西要抹腻,抹平再喷漆。喷漆人手拿砂纸心向党,把车壳喷得亮又光。全是人工。
当时我们三十八个人分到了机动车修造厂,厂址就在西安从北向南进城的北门旁边,巍巍古城墙就是我们厂的后墙。工厂大门是几根粗木棍穿着粗铁丝做的大门,进门右边两间房,一间是党支部办公室,书记在里谁兼办公。一是人事处办公室。把支部建到连上,是共产党的首创,把党支部办公室建到传达室大门口的拐弯,是我们厂的发明。你敢迟到,书记看得很清楚。进厂上坡,进门下车,骑自行车,每天上班,一周六天,天天出汗不用擦,每月挣十八。可以买三十六碗羊肉泡。
前几天一个当年一起做工的女工友历尽多年找到我,说起我们一起敲铁皮的日子,让我觉得胳膊现在还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和铁皮较劲,完全是神经有病。每天举个木榔头对着铁皮敲,满怀激情敲,敲出个槽,敲出个弯,敲出个车前脸。当年有首励志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活热的心很好玩,跟着老耄学扯淡。要是对着铁皮敲问: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肯定用榔头敲出声:我操你大爷。想想那些党安排的日子,想想人身没有自由,自己不能想到哪就到哪,想怎么谋生就怎么谋生,那叫什么生活?威力无比的共产党,是怎么样把几亿人全变成没人看管放着风可以天天回家的犯人。犯人还对看管说:看管看管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我上中学的时候,念书很行;但敲铁皮真的不行。写字跟抡锤,毕竟不是一路功。所以当上级叫我去机关学习,写鸟蛋文章,我也去,批彪哥,批宋江,批死人,只要挂个工人名分不抡榔头干什么都行。几十年的“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害里取轻。“路漫漫其修远兮”,日子过得好慢。当年要有现在的修养,我根本不会去给党贴大字报,当什么罢工领袖,跟共产党讲人理,当时误以为党会讲人理,误以为耄主席的语录是真理。事情的原委是,我们进工厂八个月都不分工种,大家每天都跟没头苍蝇一样,学不知道学什么,干为一天六毛钱。我当时血气方刚,特别追求正义。就想问问党支部:你们安的什麼心?当年就为分个工种,背后的“走后门”,送礼,道道多死。大字报贴出以后,党支部无言以对,很快就分了工种,我被“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分到了艰苦的钣金车间。这也是我的本愿,为民请愿,为众出头,不是为自己的好处。
所谓钣金,就是负责车壳,全人力打造,每年七十辆车壳,不轻松。十几个人,九男三女,最长的五十多岁,最小的差不多就是我。寒冬腊月没厂房,因为声音需要跑。穿个破棉袄,扎个粗麻绳,滦平栾副官,我等耄泽东时代的青年。有时候我老爱掐掐自己。能从那个时代活到今天。荒唐,滑稽,一如既往。三十年河那边,四十年河这边。一也回到解放前,一晚回到改革前。革了改,改完个。有钱了的中国还是选择无限期的国家主席。或许让机器人当主席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等下一次“柳岸花明又一村”。
一九七六年,在现代中国人的脑子里,是不会忘记的。四十二年前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不是七十八了。一月,周恩来死了,当时的人民都认为周是好人。九月,耄泽东死了,当时我想很多人都已经认为他是坏人了。他让中国穷折腾,他让人民没指望。忽而还有,他最后出来,眼睛迷蒙,拉着马科斯夫人的手想找个地方下嘴。后来他指定的接班人把他老婆连带王张姚全抓了。霹雳一声震那天响A,十月秋风刮北京A。再一年的冬天,高考招生。我被招。三年的工人生涯结束。我一点也不认为那三年有一丁点好,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万岁的青春被糟蹋。没有地方伸冤?活该倒霉身在那个时代。“一分为二”胡扯,多少好事被人为变坏。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扯完一淡,再扯一淡。不清算。时间合适,温度合适,就再来一遍。然而,人只活一次。(完)
[em92][em92][em92][em92][em92][em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