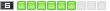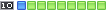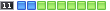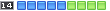岁月旧稿
雷 雨 洞 庭
-----随农场文工团在茅草街剧院
文/叙事老人
急雨穿芦顶,沉雷袭妝台。
清歌发作呼,惊弦有余哀。
屋漏无干处,回旋泥与霾。
魍魉无信义,家书徒悲摧。
佳人具慧眼,忐忑失英才!
昨夜人造肉,菘也属芸薹(几片黄芽白)。
屠牛厨下女,鹑衣若痴呆。……
俯首独沉吟,板起泪满腮。
但见洞庭水,鼓荡扑面来。
光怪满前路,厄运忍安排?
敢有冲霄翼,涵虚为君开!
-------1962年于湖滨茅草街 2016/12订
注、涵虚:水天一色。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
板起:起板。板鼓又叫班鼓,戏曲乐队中的指挥乐器。板鼓一响,百乐和鸣。
-------------------------------------------------------------------
这是一首沉积心头的即兴诗,我想把它留在美华论坛,以与发表过的一起汇成比较完整的记忆。美华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谢谢美华论坛!
这是一段历史,这一段既违反程序正义,也违反实体正义的一纸行政措施就把若干万人投入牢狱劳改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
相信历史不会重复!
这里不是夹皮沟,这是一个富庶的农场,而且是在相对优厚的总场部颇受善待的地方。
1、农场:大型国营农场。(缘起于1955年劳改犯人的围湖垦拓。曾是劳改场所亦称监狱、军垦基地、部队五七干校、安置柘溪水库移民场地)。现在是常德市下辖的县级西湖管理区。
我1959年来这里,曾在农科所,并给农场技校学生当老师上课。后来留在文工团,在总场部与来参加工作的大中学生和其他演员一起生活,排练、创作和演出。在这隔世的特别囹圄中,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前,反而相对平静。
农场富庶,在1961年困难时期,省城一些单位陆续跑来这里打通关节,弄一点鱼肉禽类乃至藕菜回去改善生活;仓皇巴结,络绎于途;其中就有我原单位的事务长罗琼。那时他们家家户户在城市住宅阳台上养兔子聊作补助肉食来源,那种腥臭就顾不得了。
时粮食与食油定量普遍减少,全团唯有我因为运动开头就已经积年旧病体弱加上单位画地为牢与尔后的折磨,这时双腿浮肿;这里每月发给我一斤食油说是知识分子政策。这是一份心领的宽厚。
我被宣告重获自由。
我那个原单位,离开时曾清楚地说还得回去,我的公职在那里。这时却来函说正值精简机构、城市下放时期,不好安排;一个省级国家单位,还说下无分支机构也无法安排;说得轻巧,有何诚信可言?而我远发配在西部的哥哥经历干部农场的强劳与饥饿双目失明继而因为政治歧视离婚,妈妈抚养幼小的侄女自己却积病益发沉重以致卧床不起。
还是这个原单位,若干年后不得不为我办理平反时派了两个人去我所在的市,却对人说要搜寻我有没有过失,而后对我说我回去后的工资要按照二十几年前在那个单位刚过实习生的级别。被浪费了二十几年最有创造力的宝贵时光,未见有丝毫的补偿;派人来为做错了的事平反,没有丝毫忏悔抚慰的表示,反而颠倒日月。他们显然心有不甘,而又自以为始终能轻易决定人家的命运!
而我早已不是轻信的昵称“三毛伢子”的青少年人,我年过四十,拖儿带女!我已经过严酷的生活证明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连带一帮人。无情的磨砺反而激发我的尊严向上,我无可幻想并不欣赏那些自以为高贵实则猥琐顽固的小人。
我不羡慕他们!
由于家庭和所受的教育,我挚爱自己的国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它竭尽心力。这时我正渴望有所创造。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我的同学与同辈人能做到的,我一定也能做得到。我无可挑选,不可能着意于城市的大小和地域的高低。
我这时已在全国业界崭露头角,倒是我所在市的市委书记,前一年在灯光运动场的万人大会上双手发给我市级先进工作者奖状和奖金,这年破例不设劳动模范。这时又因为我通过了多年后首批专业机构的职称评审,而人事部门以我并无公职存档无法备案,这位市委书记立即发话赶快派人去为我平反。这样的关怀于我一个沉沦于苦难中的人不能不感动,尽管我的被平反是在中央纪委的催促下半个月就得到落实;缘于我曾在省委机关报上发表过一篇小品文被猜忌、构陷却实在没有任何的乃至思想的错误,连口头与私自的扎记随笔上也没有。
我无须抉择,于是留在了这个市,工资自然延续;要原单位将我的公职关系转了过来。后一年我国外的亲属要回来探视,我为住房问题报告市长,几天内市长就派秘书送给我新建科技村的房子鈅匙。我的工作与生活并未因而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我已经完成了国家经委下达的课题,课题经费五万元;我因为尚未平反,身份没有着落,难以用自己的名义报请验收。我所在省和市也另题下达科研经费共四万元。国家计委经费五万元的专题也正拟这时下达,都是指定得由我来完成的课题,我自然不会撒手不顾。我已经有自己的实验室,有了花一万多元购置的材料试验设备,有实验加工用的专用机具;还花费一万元自行撰写采集和藉自己掌握的多种外语综合世界业界成就编译了四期《技术通讯》交换给全国的省级图书馆、情报所、大学与科研院所,后来主管部科技司还曾提议要我这里承担一个专业的情报站。尽管我当时所在的只是一个小厂,上海、中南、东北等著名学府自动帮我免费测试验证,我并非孤立无助。
而后原单位的刘人事处长却来信要我不要“骄傲”,还是回那里去和他共事好!几乎同时友善的原同事转告我,国家本就有了政策,平反后的工资级别可以按照现有的工资调整。
甚么叫 “骄傲”?甚么是骄傲?难道我几十年的苦难是因为当年的少不更事“骄傲”了吗?他们不知道人不妨艰苦地生活,更有人宁愿艰苦以寻求尊严的生活!这样的寻求者大有人在!只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从来抹杀这份尊严。
未必清一色的不通情理。可是一些有点权势因为欺凌弱者得到过畸形满足的素质低下者积性难改;他们不知反省,不识羞耻,不具备易位思考的凡人的柔肠,要他们懂得人生而平等,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教化与教训!
那时的平反许多都在几年后再有一次彻底的平反。
2、1962年,我已在读shami送我的前朝线装版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这一段历史见长诗《shami 你在哪里?》)。全五言的《古诗十九首》讲究押韵,而对于平仄对仗以及韵数没有严格要求。
3、1961年后,已吸纳众多大中学毕业生的文工团中骨干人员多已被宣告恢复自由,于是开始去周边的南县、汉寿县与各公社演出。演出除了歌曲、歌剧、花鼓戏、曲艺积累丰富,大型剧目有《洪湖赤卫队》《春雷》《三里湾》《刘三姐》以及《古老的战歌》种种。这时候,灾害三年犹有余悸,汉寿城关仍有吃大食堂双蒸饭的;各公社借请演出添点喜庆色彩,与社员们集体同庆。却见那宰牛的女子神色悲戚,衣衫褴褛;宰杀的是一头半大的小牛。我们晚上演出后会有一顿夜宵,通常是再加吃一顿饭。在农场生产队巡回演出这时也有吃一顿满当当的红薯或是煮大豆的;场外的公社远不如农场,这时的夜宵有的就是“人造肉”。
这里的“剧院”就是芦苇盖顶茅串紮就的一个大茅棚。
后来由省武警总队长某少将发起,我们还去了省城演出一个月,受到轰动一时的欢迎。据说少将是因为喜欢,想为这个团找出一条能够持续下去的路子。而到了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藉能从全省落难文化人中挑拣的机遇汇聚力量偶然发家的文工团的未来已经屈指可数了。
文工团这时搞了一次评审,将已经转为职工的几个被认为历史问题严重的人重新戴回帽子,包括从湘西党委来的满口阶级分析颇得看重的老张,他曾当过日本鬼子的小翻译。而在不久前,在大礼堂总场场长的讲话中,还在点名说两个刚解除劳教的小青年还可以争取加入共青团;就像苏联卫国战争英雄,进过工读学校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那样。一个是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的学生,因为在南区文化馆帮忙被发现小偷小摸由其省城著名的资本家祖父送来。另一个是衡阳饭店十八岁的女孩,因为男友打成右派被认为同情右派送来。
我已经离开回到西部家里。
4、黄芽白就是大白菜。大白菜历史上首称菘,为芸薹属植物。我当时在农场农科所时曾与也被贬去的省农科院植保专家夏松云共事,他仍在念念不忘编辑充实那厚厚的昆虫志;所以我从而知道这菘的称呼。在那时的连年大饥荒中,夏经常保存自己吃不完的大米饭,将其晒干寄往长沙家里度荒;可以想见那时城里人的生活状况。我八十年代初曾在异地邂逅他,他刚平反,被借去与澳大利亚的学术团体对等谈判。对手们多是三十郎当岁的年轻教授学者,而他则垂垂老矣!还是个技术员,相对不免嗟吁自我调侃。国家本来就缺乏有学之士,何苦要死整一些有用无辜的学人,而且挨整多年不知何日能到头?!
参阅《shami 你在哪里?》《流年 致郑玲忆昔浩劫时》(美华论坛)
——长滩拾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