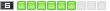第一章 凌宵楼
唐至德二年 二月十五
叶随秋再一次按住了剑柄,手心早已被汗水浸透……
仲春的和风透过窗棂,穿堂过室,宛如舞姬的薄纱,轻抚着他的脸颊,然而,叶随秋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暖意,凛冽的萧杀之气已然贯通全身,蓄势待发。再一次,他用冰冷的眼光扫视着这座厅堂,他在窥伺一个时机,一个一击制胜的机会。
这里是凌宵楼,睢阳城最豪华的酒楼,一场官方宴会正在举办中。
叶随秋侍立于厅堂的西侧,在他身前不远处,正是宴会的主席。席上端坐着一个身着四品官服的中年人,白面少须,低眉顺眼,显出四分客气,六分拘谨,全然没有主人的架势。此人姓许名远,乃是大唐治下睢阳城的最高长官,也是叶随秋的顶头上司。对于这位生性懦弱的上司,今日的叶随秋既无敬意,亦无兴趣。在短暂地打量了他一眼后,叶随秋将视线移到了厅堂的北侧,目光随即骤变,如寒冰,而又似烈火,在冷峻的外表下潜藏着彻骨的痛恨和恣意的蔑视。
占据北面次席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胖子,长着三重下巴,硕大的肚子顶到了桌案,犹如一头遍身绫罗的肥猪。“肥猪”正捧着一盘烤牛舌大快朵颐,嚼得满头大汗,一面还发出了奇怪的哼哼声。一名肩披碧绡的胡人美女侍坐于旁,一手持金酒杯,一手持白丝巾,时不时给“肥猪”喂酒擦汗。在两人的身后,站着三五个跑腿小厮以及十二个带刀家丁,排场颇为可观。该“肥猪”姓朱,是如今睢阳城屈指可数的富豪,曾向朝廷捐得礼部员外郎的头衔,世人都称他为“朱员外”。在叶随秋看来,这头肥猪和他的跟班皆为酒囊饭袋,全然不足为虑。真正的麻烦在另一边——
在东面的次席上,踞坐着一个身高九尺的黑壮汉,尽管同样是服锦绣,戴金玉,但古铜的肤色、钢铁般的肌肉、以及放浪不羁的举止无不显出其江湖强人的本色。此人姓杨,本是关东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某些缘故,如今也成了睢阳城的巨富,还领了将仕郎的虚衔,俨然跻身朝堂之上。他的身后同样也有十余名武装保镖,大半是跟他出生入死多年的亡命徒,武艺虽未臻一流,但也不可小觑。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些保镖,要想动他亦是不易。叶随秋早已探知,这位杨将仕早年得遇异人,练得一身硬气功,一旦施展开来,寻常刀剑甚难伤他分毫。叶随秋很清楚,今日之事若欲成功,必须先行击杀此人,而杀他的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在他戒备最为松懈之际动手——趁其尚未运功,直取要害,一击必杀!
然而,叶随秋的忌惮还不止于此。令他隐约感到不安的,还有另一个人。此人一直孤零零地坐在南面的末席,身边只有两个酒楼的侍者。他的年纪与许远相仿,最多五十来岁,虽同为官僚,却穿着一身朴素的便服,头戴玄色襆巾。其人气质与许远大相径庭,他的眼睛并不大,双眸平静如水,一缕长髯随风轻摆,神情随和淡泊,举手投足看似平常,实则暗藏渊停岳峙之势。“此人城府极深。”早在踏进这座酒楼之前,叶随秋就做出了这个最基本的判断。事实上,今日的这场宴会是由这位大人一手安排的,许太守只不过是代为做东而已。然而直到现在,叶随秋都未能明白:这位大人宴请富商究竟是何用意?是为笼络人心,还是为了催缴军粮?他明明已贵为睢阳城的实际统治者,却为何还要韬光养晦,甘居末席?最重要的是:如果自己动手复仇,此人是否会出手阻止,使自己功亏一篑?须知,这座楼里里外外上百名卫兵几乎全都是此人的亲卫队,各条通道都被封锁得严严实实。今日即便行刺成功,要想全身而退亦是难如登天。
窗外的嘈杂声打断了叶随秋的思绪。他不禁往身后瞥了一眼。
不知从何时起,楼下的街道上已聚集了一大群平民,至少有数百之众,队伍排到了三条街开外。这群人以青年男子为主,清一色的布衣打扮,显得很有组织。他们用粗竹竿撑起了条幅,上书一排红色大字——“誓与睢阳共存亡”,不知是用朱砂还是用狗血写成,总之,颇有些触目惊心的效果。
在凌宵楼周围戒严的众军士神情紧张,如临大敌,在校尉的指挥下用长枪结成围栏,拉出一条警戒线,将集会的人群拦在了距离酒楼三丈远的地方。
“誓死保卫睢阳城!”
见成功引起了楼上人的注意,示威人群开始高喊口号。
“守望相助,共赴国难!”
叫嚷声虽然喧闹,却也不失齐整,貌似有什么人在暗中指挥调度。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为富不仁,猪狗不如!!”
口号愈发露骨,这场示威的针对性似已不言而喻。
叶随秋无心继续观赏。在确认楼下的骚动对自己的行动不构成妨碍之后,他将注意力放回了宴会厅。
席上的两位贵客终于有些坐不住了。尽管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无耻之徒,但面对如此明显的挑衅,任何人都忍不住想要有所回应。
“嘛——我说,许大人啊——”朱员外先开了金口,他的声音又尖又长,活脱脱的娘娘腔,“今天这排场太大了,哼哼,小人可消受不起哟!这个纳捐嘛……照理说也是吾辈的分内事。我们生意人嘛,要想混日子,还不得靠朝廷和各位大人罩着?只是嘛……这次不太好办呀……大人下了封城令,小人的铺子已经两个多月没进项了。嘛,家里现在也就只剩下些口粮了。所以嘛,这次的救国捐嘛……嗯,嘛……”
随着他的话语,朱员外塞满脂肪的下巴不断抖动着。尽管早已司空见惯,叶随秋还是感到了阵阵恶心,恨不得马上一剑穿了它,把这块肮脏的肥肉钉在椅背上。
“是,是……本官知道,大家都不容易……”许太守挤出了尴尬的笑脸,“……国难当头,还请各位勉为其难,那个……共度时艰……等平了叛,朝廷是不会亏待……”
“哼——朝廷?!操他妈蛋!”一个炸雷般的声音打断了许太守的话语,杨将仕冷不防开了口,看来这位前江洋大盗已经忍了很久了,“你不说朝廷则罢,一说老子就来气!这李家朝廷到底给过咱们甚么好处?打前年儿起,老子前前后后缴了几千石谷子,本想捐个官儿当当,下半辈子吃几天皇粮,可结果呢?没成想只换得个将仕郎的虚位子,连他妈个屁用都没有!今儿你又来问咱要粮,哼哼——我说许太守,你们当官儿的胃口也忒大了吧?!这位大人,你说是也不是?”
作为回应,南席的美髯公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似乎并不计较对方的无礼,顺道还向对方举杯致意——那是一只薄如蝉翼的夜光玉杯,盛着半杯葡萄酒,酒色殷红,宛若鲜血……
“为了这睢阳城,咱们好歹都出过钱粮,外头这帮小畜牲出过甚么力?”杨将仕愈发口无遮拦了,“哼!一群癞皮狗,整天只会乱叫,甚么忠君、卫国、杀敌,哪个不会喊上两句?有种自个儿上战场去啊!一见血还不都他妈怂了?没骨头的贱种!要不是看在两位大人的面子上,老子早就下去一刀一个,全他妈给他咔嚓了!实话告诉你们,这种货色老子见多了,别看他们像模像样,只要随便剁掉两个,剩下的保准屁滚尿流!想当年,老子……”
借着酒力,杨将仕扯起了他那段大逆不道的发家史,说到激愤处,不由双臂挥舞,指手画脚起来。
叶随秋死死盯住了目标,等待着即将出现的破绽。
“嘛——杨大当家干嘛和毛头小伙一般见识?也不怕失了我等的身份?来来来,喝一杯,消消气嘛——”说着,朱员外将胡姬递来的美酒一饮而尽,顺势在她的酥胸上捏了一把。胡姬冷不防一声娇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几个下流小厮忍不住笑了出来。杨将仕方才还怒气冲冲,见状也不禁莞尔。
叶随秋的右手已然充分舒展,连绵不断的气息自掌心发出,直抵左腰的佩剑……
“……讲到这帮小年青嘛,对他们那点儿小心思,本人还是知道一些的。这毛头小伙嘛——就是虚火旺盛,要是没地儿泻火嘛,呵呵……自然就容易出事情喽!你说是不是——小肉肉?哈哈……”说着,朱员外一把搂过两颊飞红的胡姬,出其不意地揉起了对方的丰臀。可怜的美人正用手护着胸部,全然没料到这招,不由得又是一声惊叫。
“哈哈哈……朱胖子你说的倒也在理,有句老古话怎么说来着……饱汉不知饿汉饥,哈哈……好!不管这档鸟事了!来——咱们干!”杨将仕心情大好,冲着对方举起了大海碗,脖子一仰,开闸豪饮起来……
就是现在!叶随秋长刃出鞘,人剑合一,自西而东,横穿厅堂,发出了白虹贯日的一击!弹指间,剑锋已没入了对手的胸膛。
“你……呃……”杨将仕一声闷哼,瞬时面如死灰,酒碗从他的手中滑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离他最近的两名保镖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握住了刀柄,然而,他们已经没机会出刀了——一道白光闪过,两人的咽喉各多出了一道血痕。不知何时,叶随秋的左手已多出了一柄短剑,短剑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圆弧,从反手转到正手,以旋风之势割断了两人的喉管。
一击得手!接下来该轮到肥猪了!叶随秋正待收回长剑,却发现兵刃被一股莫名的强力吸住了,宛如生了根一般,任凭自己用尽气力,也无法拔出分毫。只见将死的杨将仕正死死盯着自己,神情绝望而狞厉,浑身肌肉剧烈地抽搐着,皮肤早已变成了紫铜色——他用最后一口气发动了护体内功,将袭来的兵器封在了胸腔之内,意欲与刺客同归于尽。
就这样,叶随秋失去了最佳时机。
短暂的震惊之后,在场的诸人都开始回过神来。
官兵们全然没料到这场变故,在没有接到指令的情况下,一时间都逡巡不前。
“来……来人!救……救……”朱员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早已是语无伦次。
转眼之间,在场的众保镖纷纷亮出了刀剑,形势急转直下。
“只能赌一把了——”叶随秋当机立断,短剑脱手飞出,目标三丈开外——朱员外的咽喉。
朱员外一声怪叫,推开了身边的胡姬,借着反作用力避开了要害,短剑只插中了他的肩头。硕大的身躯侧翻在地,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呵,这运气……只能空手夺刃了么?”面对步步紧逼的保镖,叶随秋露出了一丝苦笑,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兵器。
就在此时,厅堂的南面传来了玉器的破碎声,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只见南席的美髯公已经站了起来,依旧是一派气定神闲的风度,手中的玉杯早已化作碎片,深红色的液体从掌心点点滴落……
“全军听令——”他终于开了口,声音虽然不高,却让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动手!”
话音刚落,一支羽箭从他背后的窗户射入,精准地击中了对面的朱员外,贯穿了他的猪头。紧接着,早已占据有利位置的数十名精兵势如饿狼,一涌而上,将朱杨二人的随员杀得七零八落,有如砍瓜切菜一般容易……
片刻过后,宴会厅便恢复了平静。这场鸿门宴的宾客悉数倒在了血泊之中。
叶随秋毫发无伤地立在尸堆之中,眼睁睁地看着军士们割下朱杨二人的首级,装入金盘,献至南席座下,他心中一阵怅然,五味杂陈……原来,今日的一切都在某人的计划之中。这根本不是刺杀,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屠杀。双方的实力全然不成比例,结局从一开始就已预定了下来,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悬念。如此看来,自己的复仇之举倒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了,甚至,还平添了几分滑稽的意味……
“叶参军年纪轻轻,却也急公好义,本官佩服。”美髯公的话语打断了他的遐思。叶随秋没想到,对方如此位高权重,居然会记得他这个八品小吏的姓氏。他虽无受宠若惊之感,却也颇觉讶异,一时间竟无话可说。
“哦?照此看来,总不见得是……许大人?”
随着美髯公的话语,叶随秋将目光转向了西面的主席,只见许太守面色如纸,瘫坐在地,仍止不住微微颤抖,看来是余悸未消。
“呵呵,真难为许兄了。”美髯公莞尔一笑,否定了先前的猜想。稍稍打量了叶随秋一番后,他继续说道,“事已至此,本官须给睢阳百姓一个交代。叶参军请随我来——”
言毕,美髯公捧起了装着两颗人头的金盘,从容不迫地走到了阳台上。
迟疑片刻,叶随秋也跟了出去。
刚才宴会厅的一番动静显然是传到了楼下,示威的人群早已停止了鼓噪,一片鸦雀无声。人人脸上都露出了错愕的神情。
站在高台之上,美髯公将血淋琳的首级信手掷下,就像是倒垃圾一般轻松。
楼下众人先是一声惊呼。当看清了那是两颗头人之后,人群旋即陷入了巨大的恐慌。有奔走逃命者,有哭爹叫娘者,更有甚者,慌不择路,一头钻进了附近的店铺和民宅,早先的秩序和气势全都不见了踪影。而那面写有“誓与睢阳共存亡”的巨大横幅也早已被委弃在地,正承受着数百只脚掌的践踏……
与此同时,就在街道两端的路口,全副武装的大队官兵突然冲了出来,白刃出鞘,利箭上弦,毫不留情地封死了人群的退路,与守楼军士的温和态度全然不可同日而语。
面对猝然发生的一连串变故,年轻的男人们大都吓懵了,胆子较小的几人甚至当场失禁,丑态百出……
“睢阳的子民们,吾乃新任河南道节度副使——张巡!为大唐天子镇守睢阳城,肃清一切叛逆之徒!”见时机成熟,美髯公终于开了口,语音低沉厚重,掷地有声,“——现已查明,朱世仁、杨朝义二人素来目无王法,欺行霸市,鱼肉乡里,犯下杀人、奸淫、走私、大不敬等累累重罪,近日来更是勾结安史反贼,行大逆之事!囤积居奇,扰乱官市,且暗聚亡命之徒,密谋发动暴乱,妄图助反贼夺取我睢阳城!真乃恶贯满盈,罪无可恕!!本座与许太守已饬令法曹,将此二贼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听到这里,叶随秋总算是有些明白了:这位张大人之所以要拖上自己,全然是为了借用自己“法曹参军事”的微末头衔。那么,如此计划究竟有何深意?为了分担杀人的责任?还是为了表示对睢阳官府的尊重?抑或,仅仅是为了拉拢自己?……算了,没必要深究了。说实话,这次自己能完好无损地活下来,多半还是拜这位副节度使大人所赐。自己刚才的行为已犯下杀人重罪,按律当斩。可现如今,张巡用寥寥数语就帮自己洗脱了罪名,做得天衣无缝,不露声色,算不算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仔细想来,此人已是第二次救了自己。前一次是在一个多月前,那时睢阳城的形势比现在险恶得多。借着寒冬的余威,燕军——也就是张巡口中的“反贼”以十倍于守军的兵力对睢阳发起猛攻。由于守城主将——也就是许太守优柔寡断,再加上个别军官临阵投敌,胜利的天平迅速偏向了攻方。不过数日,包括叶随秋在内的众守军将士便陷入了绝境,眼看即将全灭。就在此时,张巡率三千援军从邻县赶到,以不可思议的奇袭大破燕军,歼敌两万余人,迫使残敌溃退数十里,一举解了睢阳之围。此役之后,张巡和他的军队便以助守为名,留在了睢阳城中,一直驻扎至今……
“……二贼之家财,皆为历年盘剥勒索,非法所得。既取之于民,就理应还之于民!”张巡还在慷慨陈词,“……本座宣布——朱杨两家之私产,除必要的小部分予以充公之外,剩余之大部,从本月十八日起将悉数放还民间,任由本邑百姓拿取!先到者先得!!”
人群一阵骚动,开始出现了零星的议论声,恐惧之情渐渐消退……
“……汝等没有听错——人人有份,先到先得,就在三日之后!此乃朝廷之特许,皇帝之恩泽!本座代天巡狩,传达圣意,岂敢有半句虚言?!睢阳的子民们,还望汝等在沐浴天恩之余,皆能感恩图报,与官家同心协力,共御外侮,捍卫我大唐河山!!”
言罢,张巡一挥手,发出了信号。街道两端的军队立即收起武器,让出了一条通路。
在观望了一番之后,示威的群众开始慢吞吞地退场。这些青年男子的神情颇为复杂:怵惕、狐疑、颓然,还夹杂着几分兴奋和期待……
就这样,就在这一日之间,睢阳城中叱咤风云的两大势力突遭灭顶之灾,双双土崩瓦解。家主的身死只不过是个开端——叶随秋后来才知道:就在凌宵楼行动的同时,张巡手下的另两支部队突击包围了朱、杨二家在城中的居所,登堂入室,大开杀戒,将朱、杨二人的眷属、家仆、门客、男女老少五百余人诛灭殆尽,只留下了四十岁以下,且无身孕的女眷——为了偿赎其父兄或夫君莫须有的谋逆大罪,这几十名女子被悉数没为官奴,开始了她们卑污的皮肉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