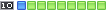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雕出来的城廓》
新疆南部腹地“楼兰古国”的北面,吐鲁番城郊也有座“城廓之国”—— “车师前国”。城墙之内有官署兵营、粮仓库房、庙宇祭坛、民房街巷,甚至坟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该拥有的,在这一应俱全。虽然,经历了数千年酷热严寒历练和风沙的洗礼,它早就变成一片败瓦残垣,但至今还能留下一座布局清晰可见、规模宏伟、保存完整堪称世界之最的古城遗址。更令人惊奇的是,据考证,这是一座被“雕”出来的城廓,现在的名字叫“交河故城”。
牛羊逐草而迁,人类依水而居。新疆地广人稀,荒漠广阔,适合人畜生存的地方不多。吐鲁番近郊的尔乃孜沟有水,自然就有人在这里安家。
有了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从高空鸟瞰整座故城的大貌。
从地球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河交汇“真迹”。从西北方向山上流下来的三道水到了这个地区汇为两支,最终在“交河城”的南头聚合,形成一个修长如柳叶的“河中岛”。再细看河道,与地球上不少河谷的形成一样,是经过数百万年水的冲刷,造就了两道宽阔平坦的河谷和两岸30多米高的峭壁。现在的东河道经修整成了一条水渠,而西河道则萎缩成涓流。涓涓流水仅滋润了河旁的低谷,那里杨树防风林绿茵如带生机勃勃,护卫着低矮的葡萄架棚。而被两河环抱着的“河中岛”却是黄土一丘寸草不生、苍凉凄切,形成强烈对比,这里“水之吝啬,风之肆虐”真令人感叹。
一条有点小陡的坡路通向山墙的缺口,原来这里就是“城”的南门。山墙上凹陷的竖坑,就是当年安置城门的地方,据说还有两是重门,真可谓是固若金汤。扑面而来的焚风,带来了火焰山的问候,六月还没有到,我们就尝到了酷热。
进“城”的路是用横放的木板块铺成,宛如一条裸露在黄土上的恐龙脊梁,直达城中一处高台。我们被很严肃地告诫:不允许离开木板路踏在黄土上。我们不知何解,只好“从命”。
“交河城”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至唐朝最为鼎盛。建城之初,正直西域群雄崛起、36国纷争不断的乱世,所以,整座城池的选址、布局都以防守为依据设计建造的。据说是由于战火不断,“交河城”毁损严重,终于被弃。但是,至今还令考古学家不能理解的是:“交河城”和“楼兰”等西域古国一样,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被“废弃”,是地质气候变迁所致,还是因战乱和人为高度开放造成?
据考证,这里留下的残墙基本都是所谓“生土墙”而不是“夯土墙”。也就是说,人们从高台地表面向下挖,就像刻图章一样,把黄土挖去形成空间,剩下的土成为房墙、宫墙、城墙,以及房顶。我见过有凿山为屋的“窑洞”,也听过掘地为房的“地窝子”,这回见识到了“掘地留墙”——在这个黄土高台“雕琢”出一座城廓。可以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古代雕塑,其建筑工艺之独特,据说在国内仅此一处,在国外也属罕见。这时我才醒悟:脚下的黄土路,也是被“雕”出来的——是文物的一部分,不能踩踏。
我虽然无法从现存的遗址判断,它是否受到当年中原城市建筑的影响,但从那些高墙深巷倒是令人相信,“交河城”建造是以防御作为设计准则,特别是街巷,狭长而幽深,像蜿蜒曲折的战壕。与其说这是座城廓,倒不如说是个巨无霸的军事堡垒。西域的群雄争霸,全民皆兵,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和民族间矛盾之深。
在峡谷中的这片黄土地上,台高风急。远处迷宫般的墙格,隐约看到当年的繁华与辉煌,高低不整的残垣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无情,凝视着脚下近处的婴儿坟场,再抬头远眺空空的城廓,虽有热风阵阵袭面而来,我心里却有点发凉,不禁想起了《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时间正借助风霜酷暑,要把这座“雕”出来的城廓一点、一点地磨平……
我们离开吐鲁番一个月后,那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交河故城”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将受到最好的保护。我虽然没有机会见证那里举行的“丝绸之路文艺演出”和“千车万人游故城”的庆祝活动,但“交河故城”早已成为我心中的名城,并刻在我的记忆链上永久留存。
[ALIGN=CENTER][/ALIGN][B][/B]
本文在《世界日报》“上下古今” 2014年9月13日、14日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