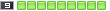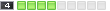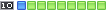12
|
|

|
||
[小说]右派黄秉一
[ 这个贴子最后由湖湘思者在12/20/2012 9:37:22 PM编辑过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自由
|

|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
||
| ||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