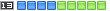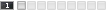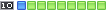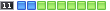文/心之初
我英俊少年时,爱刮光头,觉着铁血男儿,就该把头光。手术容易备皮,动刀少些犯愁。也许我生不逢时,没赶上打仗,常想和先辈一样,体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能和鬼子身子贴着身子肉搏,那人生该有多壮丽?
人没法决定自己生在几时,只能凑合着活,赶上啥时代就按那时代的活法活。中国时代变化快,人没辙,只能“跟着感觉走,拉着梦的手”。年轻时,拉着梦的手过活也还行。
也许人不济,也许种不好,过了“天命”,就觉着自己越长越像袁世凯。有时很伤感,好在世凯当过几天皇上,象像又何妨。我就把我圆圆的脑袋刮得更欢实了,弄的老婆常常都不爱答理我。又好在我饭做得不错,任她不爱跟我这和尚睡,却也还爱跟我一起吃。
我第一次把头刮光光是我十九岁,那会星期天我在工人俱乐部当主讲,给大伙讲“炮二平五”。记得有次讲的河北刘殿中大战上海胡荣华,就一光亮的大头,加上点神侃大攻。后来听我媳妇说那天她还从俱乐部门前走过。
男儿能不能刮光头,跟头的曲率有关,假如给你头型曲线方程,求个二阶导数,结果不该为零(大伙听说过拐点吧?)。上大学我当团支书时,把班上%40的男儿都弄成了光头,结果让我们“七七光”的在学校名头大响,声名大振,就是我那女宣传委员不爱跟俩光头一起开会。
大学毕业后教大学时,不好刮光头,为人石表。于是我留个“偏分”,还留个鲁讯胡子,弄得人女生不敢问我问题。文革时,正面英雄大多背头,头发一溜梳朝后,比如李玉和。反面人物的头型通常是“中分”,比如《铁道卫士》里的马小飞,光头的正面人物,我最喜欢的是《回民之队》的马本斋(虽然他老戴个小白帽,好像是张平演的?)。新时代了,男女头型都五花八门了。我老婆常回国弄个新头型回来,而我老不注意,常是是好些日子都没觉出来,好几次她急了问我:是不是我得把头也弄成光头,你才能看出我的变化?哎,女人的发型,我还真没注意过。
后来出国了,不感啥都由着性子,成天一“板寸”,胡子也没了。导师才比我大四岁,不想装嫩也得装点嫩。谁让咱该读书时不读书,革命来着。而革命却又不革自己的命,还一把年纪跑到美国读书,说那结结巴巴的英文,当年要不是没辙,谁会干这种“丢多大人现多大眼不说,精神受多大刺激”的事。记得当年难受时,我都唱:雪山升起红太样诶,翻身弄奴把歌唱诶把歌唱。把心态弄得和农奴一样,啥都好说。
再后来的十来年,我东混西混,南征北战,还混成个管好多美国人的领导,有时我也让自己是个光头领导。近些年,干活都更随意了,但每年几个光头,却让不少白头发长黑了。光头好,光头好,头上没毛心情好,上边的火散得快。
男儿光头,好处不少,比如当个光头鱼在水里游,明显就觉着快。天暖了,明天就去当鱼。
3/22/2010
[em50][em50][em50][em50][em50][em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