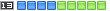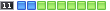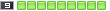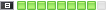文/心之初
前天,我突然接到几十年前上中学时的班主任老师的“翼鹛”,真是“天外来音喜欲狂”,心里顺便还想起杜甫两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老师打字不易,几句言简意赅,已说得我心头暖烘烘的。我赶忙打电话过去。老师和我,都有点激动。老师连问我好几遍:身体好些没有?我说,还行。我问老师:打字很不容易吧?老师答:我用“一指禅”,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看到你的回音,我真太高兴了。年过七十的老师的声音,都有点不太稳了。也是,三十五年,不到“不识数的伟人(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弹指一挥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对凡人而言,差不多已是从上班到下岗了。
写汉字变打字母(或其他),虽说汉字入机比英文入机累很多,但“有比没有强”。看老师的一小段“翼鹛”里的话,竟勾起我无限感慨。我这位老师的书法,在我的记忆里可是雄浑刚劲,灵动飘逸。娓娓里包着雄峻。这计算机帮人方便,但让人享受到美的机会却是日趋渐少。真是:昔日几十年功,今日打字“一指禅”。横竖撇捺点拐勾,左右上下宝力键。
当下地球村,村民间交流,除“翼鹛”,就是电话。从中国打美国,还是很贵,但从美国打中国,很便宜,中国也不生气。现代通讯虽说已经能把人与人拉得很近,但电话里说话,还是不能和面对面神聊相比,因为心跳离得太远。
我都记不清我年轻时和这位老师(那会中国很多“两地”,人结婚只是传香火)有过多少次神聊。
我俩经常都聊到后半夜。从“醉翁之意不在酒”聊到副总理吴桂贤;从“黑云压城城欲摧是谁写的”聊到周恩来的“节”;从诗里能不能 “不须放屁”到 “唯有宝黛入神州”。每次聊完,都觉得很精神,翻两道大铁门才能回到自家门口,全不在话下。
从我上中学的最后一学年,到我离开西安,到现在,只要我在西安,每次都想和老师见一见,聊聊。记得一九九四年,我出国快八年后第一次回国,下午去老师和我有过很多神聊的那间房。小房依旧,楼道水漫,寂静无声,黑洞洞也。我试着敲敲老师的门,不曾想竟听到“谁呀?”,我忙说:我。大概我的声音还是有点特征,老师很快给我开了门。八年离别又一见!进门一看,老师不是在做“黑房梦”(他老人家对红楼梦的研究,肯定比刘心武强),就是在等党派的联络员来接头(全楼我想就老师一人)。里边的陈设,和我的记忆几乎就没差别。久别重逢,握个手,各点只烟,能掩盖点什么的袅袅青烟后边,一双眼镜。那年我快四十,老师快六十。说老实话,我常常会想起想看到的老师的曾给过我少年时代青年时期的黑蒙蒙的心里透进过光亮的眼镜(睛)。
神聊是什么?不是读书,不是听报告;“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做文章“;不是瞎侃,更不是臭贫。是斗批改,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神龙见头不见尾的聊。聊,耳之鸣也,居然还有“深入”的意思。真是个好字。和有学问有情趣有经历有感悟的人的无计划聊天,会觉得道理传授就像种瓜;读书,太理性;书,不会哈哈;再说,人间最精彩的学问,写成了书,便已经退掉了很多情感。而我认为,精彩的学问非得是情感和理智的完美结合。名师出高徒,大概就因为高徒容易有机会和名师神聊。
七六秋雷后,我考大学,学理科了,因为人得先活着。学理工,好活。天地间,有道理;万物里,规律在物理。那会就想搏点名,“济世穷”。以为祖国四化,要靠科学。记得我拿着大学通知书的“第一时间”(新时代语言),我就兴冲冲地到老师那:我当范进了。几十年了,老师也没忘他曾有过个“范进”生。我读完大学,在大学里教了好几年书,后来又出了国,“自肩扛自脑“地在美国有了比在国内呆着多得多的人生故事。二十多年南蹿北干,东寻西找,最后发现想找的竟是从前的神聊。
年轻时我也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树雄心,立壮志”般地神聊,聊读书聊看报聊情聊玩聊爬山聊下棋聊上树聊下海,很是有趣。神聊里,思想常觉启迪,感情也会亢奋,甚至聊得有时都觉得获着点人生真谛。我年轻时,有不少这样的朋友。中学快毕业那会,我们聊,解放全人类该从那下手;当工人那阵,我们聊,怎样才能够着“十五的月亮”;上大学时,聊开个大卡(看完美国电影《车队》)多来劲,(因为认识爱因斯坦海森堡以后,才知道自个的脑袋是颗猪脑尽管周围的人们说我的脑是个灵光脑);大学教书时聊,革命的路在何方?“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出国念研究生时聊,“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红旗怎样插上大门岛?研究生念完,完了,从此单兵作战,社会是个战场,人人互相帮忙。帮忙?瞎聊。现在,朋友们大多已是太务实,实打实。不过,我有时数星星的时侯,还常想起他们。
人生有没真谛?好像和“神聊是什么”是一样的问题。
时代进步了,东西变多了。活着,成天成月成年忙活,就是弄东西,都快把自己弄成东西了:弄不着的无奈,弄着的高兴,还有不想弄的没感觉?
东西,除了实的,我想还是该有点虚的,咱中国人爱讲,“做人不能太实”,不知有没点这意思?
人,活着,除干活,得有点神聊。我这么觉着。
7/25/2009
[em96][em96][em96][em96][em96][em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