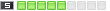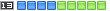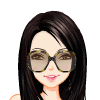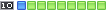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IMGA]http://static.orient-express.com/orex/images/475x300images/orex_475x300_explore_heartofcity02.jpg[/IMGA]
我一直以为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只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侦探小说里的虚构道具。直至有一次在维也纳开赴慕尼黑的火车上,我翻开一本广告,被一张阿尔卑斯云山环护的林间车行图吸引,旁注正是东快;再一张,几位法国主厨精选碎冰上肉色鲜红的三文鱼,工作月台,恰好位于巴黎东站(Gare de l'Est)。我约略记得,曾经有过一出东方快车上鸳梦重温的戏码(Romance on the Orient Express),男主角有点像克拉克.盖博,女演员一头金色锦缎,秀雅美丽。那卧铺车厢似乎是宽绰的,餐车尤其考究,仿佛移动中的上流家居。阿婆的小说人物,我最喜爱艾尔古勒.波罗 (Hercule Poirot),也很欣赏大卫.苏舍(David Suchet)版的影剧化身,不过我对影视改编,一贯不太感冒,所以那场雪封后的神秘案件,很遗憾地仅仅遗存十余年前的阅读记忆,我对哪怕道具,也没有什么深切概念。
这趟远行之前,我开始看阿婆的叙利亚行记(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开篇未几便留意到行间飞驰的东快,随后对照她的传记(Agatha Christie, An Autobiography)章节:第二春(Second Spring),车旅感悟更加繁茂,经不住撩拨,我又按下这一卷,回头重温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大侦探波罗名噪全球的著名案件,虽然,从他的角度,不过归途中一桩小插曲,作案手法也算不上专业。自此,东快情结在我这个随意读者心里,终于由隐约发酵,提携至难得热泡泡。
今日的辛普朗东方快车(Simplon Orient Express)主要往来伦敦、巴黎、威尼斯三地,亦可排入奥国因斯布鲁克、意大利维罗纳等风情小城,又或者东抵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以及伊斯坦布尔等观光要点,然而比起历史上那样频繁的欧陆穿梭,声威不得同日而语。阿婆乘东快,总要一路坐到底。首先自伦敦维多利亚站(Victoria Satation)上车,抵达多佛港后转船,上岸后取道戛莱、巴黎、洛桑、辛普朗隧道,一路东进,到达伊斯坦布尔后再转乘至大马士革或巴格达,回返时,可沿原路或北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经德语区,然后斜走斯特拉斯堡。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的路线,采用前一种。
[IMGA]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0/Orient-express_histoire.png[/IMGA]
在东快官网上,我读到,最早一次东行,发车于1883年10月4日,从法国巴黎到罗马尼亚久尔基。那时候,大约只得一两节普尔曼豪华卧厢加上隆重餐车,车厢外简要标明始末站点,以各自区分,就像小说中那样。随着车龄延长,东方快车的厢体,也演变为老爷串烧,汇聚了来自英伦及欧陆各地的古董制造。当年旅客,并不乏达官政要、贵族富商,一路咀咀唔唔莫名语言,随着窗外罗曼蒂克风景回环交迭,彼时欧陆货币分治,餐车里各路支票蔚为大观,甚至精明人士,还会来个多角套汇。我不知道如今的娇客,有多少还有阿婆那样探险猎奇的心情,需要径走到大漠深处,方才展颜释怀,现在的东快,旗下有五大洲51种营业,其中愈 40种为高格调宾馆,大抵便是把舒适享受一条龙送到家,而Exploration的成分,恐怕还打点折扣。
我去巴黎念书的时候,高速列车早已蔚然成风,而几年以后离开欧洲之际,尚不了解还有高端的一款东方快车。无缘亲身体验阿婆的座驾,未免好奇,会不会哪个座位上标明她曾经来过?如若见到,不晓得心中波澜几许。然而,在欧陆坐火车,于我也不算生鲜经验。那时候一个月里,总有一两次来往巴黎和布鲁塞尔,再要到更远一点的荷语鲁汶。红皮塔利斯常常给年轻学生打折,饶是我这样靠菲薄奖学金度日的,买往返车资,买中餐原料,买闲书,似乎从未拘谨过。
布鲁塞尔那边,有等待我的人,所以北上的路,永远心境明媚,读书或翻资料,再不然对牢电脑看肥皂剧,疾驰的列车上,风景一闪而过,而我恨不能它更快,旅行时间更短,手边不住杂碎,只要稳下一颗跳逸的心。而返回巴黎,是一定独自走到终点的,于是我更通常往向窗外,为前瞻的孤独做心理垫背,那时候,才感应到车厢微妙的颠簸,车外的油画,后退为心事的背景,我比任何别的时段都更靠近自己。
后来,我读到法国作家安娜.卡瓦尔达(Anna Gavalda)写的那段话:“当我到东站时,我窃窃希望有谁会等着我。这想法真傻。我一早知道,妈妈这个钟点还在上班,而马克绝非穿过郊区过来为我提包的那种人,但我一直存有这种愚念。
我想要有谁在什么地方等着我...这其实,一点也不复杂。”
(Quand j'arrive à la gare de l'Est; j'espère toujours secrètement qu'il y aura quelqu'un pour m'attendre. C'est con. J'ai beau savoir que ma mère est encore au boulot à cette heure-là et que Marc est pas du genre à traverser la banlieue pour porter mon sac, j'ai toujours cet espoir débile......
Je voudrais que quelqu'un m'attende quelque part...C'est quand même pas compliqué.)便觉得心声与共,尤其在川流不息,而听得冰凉时针步幅的站台上。
火车是一种奇异发明,我情愿把它视作生物,历经百年沧桑,横贯迢迢山水的东方快车恐怕更加如此。衔接着希望与失望,逗点与惊叹号,裹挟木棱窗影里的人面,犹疑忐忑的人心。当年,行走潇洒的阿婆,也一定深陷在这样的生物气氛中,焦虑,沉迷,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