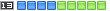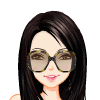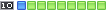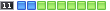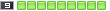在那次学农中,我们班对外形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在学农杀青的晚会上,我们班“浪里白条一种手式指挥,众多光头锃亮的齐声合唱”,更是让系里其他几个班看到了一个 “崛起”(叫雄起也行)。
“浪里白条”有两体育长项,一是游泳(前边已提到),另一是足球,因为好像巴西队有个卡卡。加上姓就成了我给他的名。他是成都人,中等个,戴眼镜,皮气好得惊人,有点蔫怪。他当时是班干部。我们班的合唱,唱的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好像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也不知是谁的主意,让音乐方面和我差不多的匡卡卡来当我们的指挥。他的合唱指挥可真的是“擀面杖吹火”。按说我们班音乐方面能人很多,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像刘芳亮,不光会使枪,也会歌唱,但就是不爱出头露像。“让杜丘跳楼的大夫”靳大侠,音乐上也很有一套,也不愿挺头(日后在全校聚餐大会上指挥我们餐桌的大声唱《外婆的澎湖湾》唱得当时全食堂鸦雀)。幕后的能人在一两天里“速成”了我们班的指挥,但“浪里白条”速成的只会一种手势。演出时我们绷住不笑,“一切行动听指挥”,光头跟着手式走,歌也唱得齐刷刷的,但“大刀”好像都砍到了西瓜上。
当年,我们自己都不是自己的,但我们的天天还是挺乐呵的。回忆点从前的事,心里就觉着温暖。就像《友谊地久天长》第一句唱的:那过去的好时光。哼起,心里就暖洋洋。其实,过去的时光就比今天的好吗?也不见得。过去,觉得《红灯记》里鸠山说的话不对,人不为己,天怎么就会诛地怎么就会灭你呢?到后来没过多少日子,党不当俺们的娘了,只管他们的亲生。到那时,哎咳,想起鸠山说得没错,就是话的度数高点。
一九七九年,是血燃风采的一年。国家在找路,路在何方?文艺在 “伤痕”,伤在人心里。人的思想都在“布朗”,像容器里的气体分子。咱伟大的振荡国家,前所未有地振荡。就像个要去刷漆提着的油漆罐,人人就是油漆分子。油漆在用以前,刷油漆的人要一阵猛晃。人在筒里给晃得热血喷张四肢抡开。那一年,日后定义为改革开放的元年。“改革开放”,当年好像还没这么说,只是画圈老人一个云手,让华政委回家练字去了。激情澎湃的耀邦,出来“领风骚”。毛主席被三七开了,继续在天安门广场睡着。
政治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克林顿的“太爱”,在那年好像不怎么招人待见了。但政治还是治着年轻的小伙年轻的姑娘。我们班那年最高兴的事,就是罢政治课成功。
那年下半年,我们政治课一如继往的无聊,教我们的是个小老太,把个马列政治经济学在“乱七”的基础上,教得更“八糟”了,用四川话讲,就是听课听得人磨皮擦痒。但那会人都知道:活着就得忍耐。也不知是谁,有可能就是我,说:我们不能再忍耐。“星星之火”遇着干柴。烈火烧干柴,是鬼也害怕。
我去和政治老师理论:政治是不是科学?
政治老师说:当然是。
科学有两个特怔:可验证,可讨论。政治可以什么?我再问。
教我们政治的陈老太不跟我理论了。后来是换人接着讲还是就不上了,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罢课成功了。真可乐。(待续)
[em73][em73][em73][em73][em73][em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