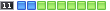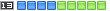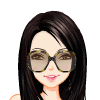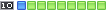似水年华(六)
有一个夏天,区工业举办了一个通讯员学习班。厂里就派我和纺纱车间的“墙报编辑”常戎一同前往。在这之前我和常戎最多就是彼此知道对方的名字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可是这回参加这个学习班,我和她可真算是朝夕相处了整整一个月。
说起来,常戎她人长得挺秀气,皮肤白皙,人一激动,不管高兴还是愤怒,眉毛嘴唇都会泛红。但她说话嗓音沙哑,走路喜欢把手揣在兜里,佝着背,说话从不啰嗦,最喜欢用三五个字解决问题。而且她的字写得极好。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相信字是敲门砖的古训,有事没事拼命练字,可是那字写得好不好,有时也不是靠练就能练出来的。我觉得她还是挺可爱的,有一股男孩子的“英气”。
在学习班,每天来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省报的记者。我记得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那时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概念,从小在一种教育下成长,哪里会知道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区别?但应该说这一个月的学习还是有收获的,至少我第一次听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第一次知道英文里新闻的“NEWS”就是东南西北,就是天下大事的意思,(N—North, E—East, W—West, S—South);第一次知道新闻报道其实就是个根据总编的要求,搜集必要的素材,然后编织一篇谎言。真的,我决不是耸人听闻,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在学习期间,记者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份作业,让写一篇一场火灾的新闻报道。背景可以是任何地方,工厂,农村,大街小巷……。我心中一喜,因为我肚里正好“有货”,在前不久我正好经历过一次有惊无险不大不小的的车间火灾。于是我拿起笔就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某年某日,某纺织厂织布车间,因为电线老化发热导致房梁上堆积的棉花粉尘燃烧,火焰顺着房梁迅速的蔓延,如同几条毒蛇一般同时向地面正在一线战斗的工人战友扑来;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掩盖了最初发现者的惊叫声,很多人仍然专心的埋头操作……,只见已有五六个月身孕的小芳抱着灭火器摇摇晃晃地从外面冲进车间,机修工张国强,车间里唯一的男人,用跳高运动员的身姿徒手跳上离地几米高的总闸关掉了电门,车间徒地安静下来,在黑暗中火焰更显得触目惊心……。大火在大家齐心合力奋不顾身的努力下渐渐熄灭了,等车间主任闻讯赶来,我们无产阶级工人弟兄已经勇敢地扑灭了大火,避免了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胜利地保护了国家财产……,云云。我挺得意地交了稿子。
可没想到我这篇稿子成了“反面教材”了。
记者张老师说,报道一次工人阶级弟兄奋不顾身英勇救火保护国家财产的生动事例当然是个好题材,但是由于这篇文章首先没有体现阶级斗争,要知道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没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没有和阶级敌人的斗争,这个报道就是失去了主题;第二,报道中没有体现党的领导,党员在救火当中的先锋带头作用,使你这篇文章没有了灵魂。既没有主体又没有灵魂的文章,报社能给你登出来吗?
我很羞愧,但我也很困惑。难道我得写我厂某个国民党残渣余孽趁我们上夜班人少,爬上车间的房梁点燃棉絮粉尘,(我们厂倒是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可他们早就老得只剩下喘气的份了,哪还爬得了高?)车间转业军人共产党员机修工张国强,(可他不是啊,他连团员都不是,别说党员了。)勇敢的与敌人搏斗,现场抓住了蓄意破坏的阶级敌人:可这还是没有党的领导啊,当时车间只有我们几个小年轻上夜班,党的领导都在为革命养精蓄锐呢,我的想像力实在有限,实在编不出来了。常戎说,这样吧,危难当头,咱们车间立刻成立了党小组……,没有党员?可以考虑火线入党,可谁来批准啊?!最后那位记者张老师说话了,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嘛……,可是这怎么个浪漫主义可就是个学问了。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干什么也不能干记者,连自己都骗不过,怎么去骗别人!
除了上课,我们也要出去“采访”。所谓采访就是事先定好了题目,理好了大纲,然后填上真实的人物地点,好一点的话,争取多加点生动的细节,不过这也得小心,一不留神,就会冒犯主题而被毫不留情地删掉。
出去时,我和常戎总是在一组,走路或坐车,难免无事闲聊。有一次她问我,你相信爱情吗?那时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我却胸有成竹地说我当然相信!她问我,你又没有经历过,你怎么知道?我就热情洋溢的把我在小说里读到的故事一个一个的搬了出来,她狐疑的看着我,却热切地想知道每个故事的结局。碰上Happy Ending , 她就长吁一口气,如果是Sad Ending,她就会说,你看你看,你还说有爱情,那他们怎么会这样?
那时我就觉得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怪。有一天我就突然袭击说,你是不是失恋了?没想到,她马上承认了。她说她有一个在部队上的男朋友,两人交往了两年多,可最近不知何故,那个男生突然提出分手,令她非常难过。现在想起来,她那时也就是十八九岁,我十七岁,可我却做出一副很老练的样子,给她设想了那个男孩改变主意的N种可能性,可我偏偏就没想到其实是因为常戎家庭背景不好,军队审查不会通过。但这也不能怪我,因为那时我压根就不知道军人找对象都必须根正苗红。也许那时常戎自己也未必知道,但不知问什么,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常戎从此恨上了我。
一九七四年,就在我要去上学离开那个棉织厂的前夕,厂里搞了一次整团学习。气氛非常严肃,区团委还专门派了干部下来,组织我们学习,先是自我总结,然后是“互相帮助”。我们对这一套东西早已司空见惯,我开始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何况我马上就要走了,手续都差不多办完了。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常戎竟然在整风会上对我开了炮!自从我们从学习班回来,就各自回了车间,几乎没再打过什么交道,我和她也不曾有过任何利害冲突,任何过节,至少我这样以为,可她为何要这样?
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的话,……她身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却满脑子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她不但自己滥读封资修的毒草,还到处宣传毒害别的青年;……她把织布车间一班搞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突然想起曾经对她说起我们织布一班的人如何合得来,如何团结的事。当时我完全被她打懵了,惊愕茫然的望着她。可她并不看我,脸上一副冷冷的表情。可接下来,却并没有人跟着响应,我真的非常感谢我当时的那些工友姐妹们,大家沉默着,本来我应该说点什么,但我脑子一片混乱,也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主持会议的郑书记说今天就先到这吧,大家都回去想想,明天再继续讨论。散会前,他叫我留一下。
后来这位郑书记送我回的家。他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对我说,你在政治上太幼稚,有些话心里明白就行没有必要对别人说。你明天去把离厂的手续全部办完,把团组织关系转走,不用来开会了。
我真希望这位郑书记知道,到今天我都在感激他。可遗憾的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后来听厂里的人说,常戎一直没有结婚(至少在2000年以前,不知眼下如何)。自学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调到区法院工作了。其实我也并不恨她,只是若有机会,我有点想问问她,当年她为什么要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