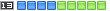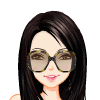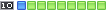李兆阳谈诗之三十:人界、佛界、魔界
日本一休和尚曾说“佛界易入,魔界难进”。佛家、道德学家也常说,“佛界”“魔界”之间,一线/一念之别而已。怎么解?
以我们这些不谈佛的人而言,佛界,恐怕就是一种慈悲、悲悯的境界,也就是在面对于轮回中悲苦的芸芸众生所产生的对众生的慈悲、悲悯的心境。佛家常说的“人人都有佛性”,“佛在心中”等等偈语,强调的就是这种慈悲、悲悯的心境。另外,佛家有舍身成佛一说,何哉?将自己慈悲、悲悯的心怀外延,达及众生众物、包括饥饿状态中的老虎,舍自己的身体为虎吞噬,解脱老虎由饥饿而生的悲苦,以成就佛境。再者,因为慈悲、悲悯的心境人皆有之,芸芸众生,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所以要达到佛境,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选择和意志力的问题。因而,一休言“佛界易入”,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是魔界呢?谈魔,自然是相对于佛界(如上)和非佛非魔境界的“人界”(我等众生、凡夫俗子的种种境界)而言 -- 与佛界相对,众生相之外的境界,就是魔界。所谓众生相,就是包含众生生老病死一概过程和感受:笑、哭、悲、与不悲,凡此种种,都是人界中我等凡夫俗子的众生相。所以,所谓魔界,就是佛界外,超越众生生老病死,笑、哭、悲、与不悲状态的境界;这样一种境界,必须是独特的、超越众生凡相的境界。这样一种境界,自然难入,所以一休言“魔界难进”。
那么,为什么佛界/魔界之间,只有一念之别呢?佛境或者佛界,以己达人,也就是把自己的佛性向外延展,以此体验、悲悯或者慈悲人界中众生的悲情苦境。而魔界、魔境则不然,入得魔界者,超越人界 -- 包括众生相中自身的凡情凡境,也超越源自众生悲苦而生的悲悯、慈悲情怀(所谓佛界),把握生命对自身的独特感受,再经由这个独特的生命感受以把握世界。所以说,魔界超越了人界,也超越了佛界,魔界是超越的、是独特的,也是自由的。达到魔界的人,把握了人境、佛境、魔境,人、佛、魔归于一身。所以,入得魔境的人,是自由的人,进入了自由的境界,佛界与魔界之间,对这样的人而言,已经毫无阻碍,因此佛界与魔界之间,“一念之别”而已。
魔界的另一个属性,就是不可言说。为什么?因为魔界超越了众生凡相诸般世界,我们众生相中用以表达信息和情感的语言和其他交流手段,无法表达魔境:因为语言或其他交流手段,是人界中芸芸众生基于现实的沟通的要求构建的,这类交流手段所能表达,终归只是我们众生世界中的诸般情境而已。魔界超越了众生世界,也就超越了语言,而超越了语言的情境,无法用语言表述,因而,魔界种种,无可言说。
现在谈谈诗歌。我们读诗品诗的过程中,往往专注于寻求诗中无可言说的境界。为什么?可以言说的境界和情绪,终归只是众生凡相中可以道说的境界和感受而已,缺乏独特性,因而平淡、也无味。只有独特的情境和经历,才给予读者关乎生命的独特性感受 -- 实际上,独特性体现了作品的文学价值。而这类独特性的感受和经历,因为其独特性,超越了语言,因而也无可言说。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品味诗歌时对诗歌这种独特性情境的追求,与佛家求魔境的情境相若。这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真正的诗意是一种说不清的感受/感觉,能说清的感受/感觉,就不是诗歌了。再者,许多诗人、包括笔者自己,喜欢读晦涩的诗,这类近乎逐臭的阅读嗜好,其原因恐怕也是基于对独特性诗意的追求。
除了诗歌外,“魔”与我们对其他形式的艺术的欣赏也息息相关。前几天看电影《海角七号》。电影里有两个主人,已经撤离台湾的、已经辞世的日本人老师和当代青年、台湾歌手阿嘉。日本人爱恋台湾女子、也是自己学生的友子。这个故事以七封日本人书信的方式,隐形表述日本老师对友子的思念和爱,以及对拆散他们的、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无奈。当代青年阿嘉的故事,就是愤青歌手阿嘉,得遇日本女子友子,与友子从隔阂、冲突、到相爱的故事。因为这段经历,阿嘉从愤青变成了歌手,友子也从一个日本女人变成了一个台湾女人。两个男人,爱上同名为友子的两个女人,一个以离散收场,一个和满。何载?命运使然。冥冥中我们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安排了这两代恋情的绝然不同的结局,让人感叹。电影中阿嘉有唱歌,修改歌词等等情节,但阿嘉的歌,其愤者,听起来也就是当代流行的愤怒之歌,其柔者,也还是当代流行的情爱之歌,这些歌曲,在笔者听来,虽然顺耳,但也就是人界、众生相中的凡音而已。而另一首歌,是日本歌手中孝介唱的,应该是表达日本老师和台湾学生的离散的恋情吧。这首歌虽然被弱化,听在笔者耳里,却隐隐有魔意、摄人心魄。笔者称之为魔音。
李兆阳 2009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