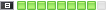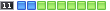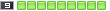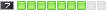猫儿所“凑四首”高水平,比我好;“刚好九首”更好,好兆头,友谊长久。谢谢猫!!!
谢谢风中秋叶兄指点。 风中秋叶兄的点评,深合我意。
提上旧帖倒有一个好处,可把《美华论坛》当年之繁荣直接呈现眼前。那么多评论家、作家、诗人、画家,齐聚美华,那气氛健康高蹈友善。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某一天齐刷刷走了,这是重振美华要想的事。总结经验教训才有新生。
美华必将再繁荣!
我不好意思跟自己的旧帖,有怠慢处诸兄体谅。但朋友们的友情我不会糊涂。
这组《如梦令》,正巧这个月以《赠郑玲·外五首》的题目发表在《星星诗刊》下半月刊2008第10期上。(那“外五首”也都是老朋友知道的。除了《赠郑玲》《贺新郎》是几十年前写的。另三阕词都是在《美华论坛》练手的产出。可见美华对我的帮助很大)。
这期《星星》还发表了我用“罗宾”之名写郑玲先生的千字文《熬过了的青春》。现录如下:
赠郑玲(外五首)
陈善壎
自识君来未有家 头颅将取走天涯
宜兰园里窗前月 野桂山中岭上霞
慷慨许同无定骨 绸缪还化杜鹃花
书开夜半人初静 语共灯前影正斜
宜兰园、野桂山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那时白天要出工要挨斗要游街,只有到晚上才有空看书、谈天,故有“书开夜半,语共灯前”句。不知情者或有很“诗”的理解,其实是很惨的。很惨又写得“美”,此文人伎俩也!
贺新郎
不弄辞章久,偶临溪,番惊两鬓,飘霜时候。半世磋跎谁慰籍,好是故人依旧;幸还嗜, 烟和醇酒。检点平生无事业,被朝风暮雨调摆够,酸甜苦,辣都有。
斯须变幻如苍狗。抖精神,交谊舞帝,卡拉歌后。志在皮囊求一醉,问讯水肥山瘦。又羞见,从前师友。岁月空抛今已矣,夜深时,诵得楞严咒。迷或悟,难参透。
八十年代后总算安定了,有筋疲力尽的感觉。
沁园春 回长沙
这次回长沙是2006年4月12日。上午出发时气温摄氏31度,晚上到长沙只7度。我一身单衣单裤,冻得敲。朋友见了说我既年青又前卫。
有客南来,冠敝裘轻,人逢曰癫。也迎风写句,临流赋景;山岚向暮,冷雨池边。半世窝曩,三餐勉强,一碗粗茶一袋烟。争知我,已千疮百孔,不是从前。
通衢大道流连,又岂料离家四十年。笑文心细逐,词章长短;年时襟抱,莫问苍天。纵有贼心,终无贼胆,市井磋跎岂偶然。空回首,见湖湘寺古,触目皆禅。
夏云峰
远处车河,身边闹市,懒看芽新叶嫩。春来早,风轻雨冷;人偏老,筋疲力尽。
想平庸一世糊涂,纵饭软茶香,终难来劲。有寥落诗才,萧条文笔,输却歌筵红粉。(1)
不值一钱心自问,是绝地求生,装疯装病。抽支烟,伤人肺腑,喝杯酒,了无嗔恨。 好容易熬到如今,竟忘了猖狂,烹贤煎圣。此后若荒唐,先勘死活,再去谋篇布韵。(2)
(1)有感数千字稿酬不及三陪一曲润喉。
(2)我的作品要发表难。多因题材“敏感”。今后要先看能不能发表再动笔。放聪明点,老实点。
偶感(步人韵)
一世苍惶何所期,粗蔬淡饭已如斯。
闲时啸傲无人会,老境吟哦有汝知。
岂料昏黄交胜友,聊将懵懂步君詩。
莫嫌词鄙情堪重,只问文章不问誰。
熬 过 了 的 青 春
罗 宾
在很长的时间里郑玲没有相对安定的居所,这段时间实在太长,以至她没有保存任何旧物的能力。她甚至拿不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照片来。关于她的青年时期只有去记忆中搜寻一鳞半爪了。
郑玲能记得起的最早与诗有关的事,是一种叫《黎明的林子》的没有封面的用很黄的纸印刷的诗刊,后来这小小的刊物更名为《诗垦地》。当时她读初中一年级,这时候就喜欢读文学方面的书了。她特别爱读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以及文学大师们的传记。她自己回忆说:虽然年纪小,居然也有些懂。这一切启发了她的追求。放学后,她常徘徊在重庆北碚黄桷树的那间小土屋附近,那里住着编辑《诗垦地》的绿原、邹荻帆、曾卓等诗人。这是非常光明的记忆,郑玲终生崇仰着这几位诗人。她最早的诗作《我想飞》也是这时候写的,老师帮她发表在《江津日报》上。后来就随同一群进步青年“飞”到湖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少不了餐风宿露,少不了光着脚作几十里路的夜行军。她在游击队文工团,做些迎接解放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她的性别和年龄(小妹子),接受过进城监视敌人动静的任务。那时地下武装保护过一些文化人,她奉命陪伴过女作家白薇。这时候精神上极其充实、亢奋,算是她青年时期很美好的时光了。这“美好”是与艰辛、紧张、危险联系在一起的。
解放后郑玲先后在长沙市工人文工团和湖南省人民出版社工作,这期间有条件读大量的书。她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爱读普希金、屠格涅夫;也爱读托尔斯泰、赫尔岑。这些作品中的养份,成了她本质性格的培养基。她基本是不屈的、牺牲的、悲剧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人热情洋溢,忘我地工作、创造、歌颂着。关于明天,想到的只有幸福与辉煌。她开始了诗创作,《长江文艺》是她经常发表习作的地方;也在《人民文学》发表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江大桥诗二首》。讽刺的是,不久她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这是郑玲青年时期发生过的最痛苦的事情。记得当时她在斗争批判她的万人大会上抢过大会主持人手中的话筒大声地呐喊:“你们扯谎!扯谎!”
从此她失去了工作,她什么都没有了,都被剥夺了,正当她的青春年华。
流落到社会上之后,她认识了陈萱。他们都在城里教夜校,后来挑土挑泥沙。后来又流落到乡下去了。这期间他们一起坐监一起流浪、东奔西走。在旅途上,在风雨中,在车站的角落里,在临时驻足的农家茅舍,他们靠背诵唐诗宋词,靠讲《九三年》《基度山恩仇记》御寒充饥。后来又在湖南省江永县的大山里落户了,收成最丰的年头,两个人一年劳动的收入不过一百元。白天他们劳动兼接受批斗,晚上围坐地灶边煨红薯烤包谷。有时她会朗诵她的新作,朗诵完了便付之一炬。
这已经是在灾难中了。但在灾难中过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是灾难,它变成了平常日子。在这样的平常日子里再有灾难临头,就是更深一层的苦痛。文革中,陈萱被抓走了,整整关了一年。她独自生活在黑暗中。有两个人共处的黑暗是光明,一人独处的黑暗便是黑暗中的黑暗。一年后,陈萱获释回到她身边,她说那种感觉就象四九年全国解放一样兴奋。那就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划亮了一根火柴。那就是光明。
郑玲熬了几十年,终于把青年时期熬过去了。此后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折,到了她早已不是青年的时期才重新发表作品。我见过台湾诗人王禄松这样说郑玲的诗:“非经大思考、经大灾劫、茹大苦痛者,焉能臻此。”我很佩服王禄松先生仅凭诗文而知人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