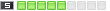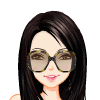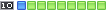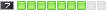想娘,从过年开始
文/邱晓鸣
娘,过年了,儿想您。
想娘的时候,总是黙黙的,不敢声张的。
一直以来,总想为娘写下一点文字,以作记念,可我不敢。怕么?是的。我是怕自已的语言,不能尽意地去表达,那样,我会后悔,甚至会觉得对不起娘。这种感觉,就象游子还乡,总想着把最好的最体面的东西,大包小包地提着,兴奋地快步跑去,叩开自家的门,大叫:娘,我回来了。多年来,我把对娘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一藏,就是十六年。
娘是在九二年冬天,因车祸,突然离开了我们。我是在不知实情的状况下,匆匆地从外乡赶回去的,面对着故去的娘,我整个人都傻了。几天里,我就象个木偶,任凭亲友们摆布着,直到娘下葬,都没有为娘,认认真真地哭上一次。
娘下葬后,亲友们该走的都走了,家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这时,我开始想娘了。那种想念,是清晰的、直接而又急切的,心口睹得慌,疼得慌,又无法释放。无奈,找来那件娘穿过的,我执意留下作为念想的衣裳,搂在胸前,嗅着娘的气息,还是不行,心里老想着找个地方,痛快地哭它个彻底才好。于是,我独自踩着雪,半夜里偷偷地去看娘。
雪好大,好厚,残月弯弯,满世界都是白的。
来到坟地,望着被厚雪覆盖着的娘的坟头,想哭,却哭不起来。我便坐下来,同娘说着话:娘,我来看你了,娘,你冷吗?我就这样对娘说着,说了许多,我自信娘能听得见的。没有风,雪夜里的原野,静得让人觉得心里空的慌。蓦地,我听见一串响动,寻声望去,是黑子,大哥家喂养了多年的狗。只见它哼哼唧唧地走过来,在娘的坟边转了几圈,停下,望了望我,然后,偎在了我的身边,用嘴亲贴着我的手。我在外地工作,照理它和我是不熟的,它却如此亲近我,没一点儿生份。狗通人性,我知道,和我一样,它也在想念着我的娘。我一把搂住它,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常言道:养儿方知报娘恩。娘呵!我廿七岁了,你的孙子,刚出生三十七天,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我边哭边喊着娘,娘不理我。
我知道,从此,我没娘了。
起风了,那风,彻骨的寒,乌乌地带着哨音,仿佛也在哭泣。
娘一共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孩子,想起来,娘这一辈子,着实不易。娘的儿女心重,手心手背的都是肉,每个孩子都牵着娘的心。我的一个弟弟,在十八岁那年,因患血液病,不久便去逝了。接下来,我的姐姐,三十九岁时又因脑瘤去逝。这一连串的灾难,对娘的打击有多大呀,好在,娘一次又一次地在苦难中挺了过来。娘很坚强,她说,穷没根,苦有头,人呀,只要活着,总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我在家里行五,娘生我时又是双胞胎。胞弟在生下十七天的时候夭折了,有传说双胞胎死了一个,另一个是活不成人的。于是,娘格外地疼我。
我从小就厌烦人,不省心。不说好好读书,还总惹事,弄得娘见天给人家陪不是。当然,我是少不了挨父亲打骂的。家里的墙上,总挂着三个鞭子,麻绳搓的,家里孩子多,那是父亲的家法,小错用粗的,大错用细的,鞭子越细打起来越痛。
放寒假了,我的成绩总是一片红色的不及格,老师的评语总是列举许多条毛病,让家长严格管教等等,表扬的大不了就是能团结同学,极积参加文体活动什么的。回到家,将成绩单递给父亲,不用说话,自己主动从墙上取下鞭子,将裤子褪了,让父亲打屁股。父亲见了,便气,打的便凶。我呢,又特犟。挨打,从不哭。父亲常常被娘拉开,我呢,仍撅着屁股趴着,怎么也劝不动。娘说,憨货,你怎么不跑呀!我不动,心想,反正,他不能打死我。父亲更气,打的更凶。娘好不容易才将父亲劝走,扶起我,看见伤痕,她心疼地说,你真是个犟种!说着,娘便流泪了。见娘哭了,我说,娘,许云峰连老虎凳都不怕,打烂屁股算什么,过两天就好了。娘笑,娘说,你个活土匪呀,娘说着,用手轻轻地摸抚着我的伤痕,娘问,疼吗?我说,不疼,嘴里说着,眼里一热,眼泪就流下来了。娘温热的手,是世上最灵验的催泪弹。娘说,你这个讨债鬼,怎么就考得这样孬呢?娘识得一肚子的字,留着没一点用处,要是能给你就好了。我笑,屁股虽疼,心里却掠过一阵轻松,父亲这一关就算过去了,寒假了,过年了,我的快乐的日子来到了。
娘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是不甘心的。娘毕竟是读了女子师范的,外婆家原先是个大财主,城里开着粮行,乡里拥有上千亩土地。我想,娘年轻的时候,对未来对爱情,一定怀揣着许多的梦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今生会选择父亲,因为,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阶层。父亲出生于赤贫的家庭,逃难至此,穷,就想着活命。我大伯是土匪,被枪毙,二伯参加八路军,战死黄河。整个家,最后,只称下父亲一个革命者。革命胜利了,一个赤贫的毫无文化的共产党人,娶了一个识文断字的成份不好的,美丽善良的地主子女做了妻子。父亲脾气丑,常常拍桌子甩板凳的吼人,娘呢,总是细声慢语,从未见她发过一次脾气。父亲与娘,一刚一柔,组成了一个家,养育了我们一群儿女。娘常说,都是命。
现在,我信了。
娘总说,儿女是娘的心头肉。我们兄弟姐妹,不知不觉地就长大,嫁的嫁了,娶的娶了。我调外地工作的时侯,小弟也参军去了,家里就称下她和父亲守着。也许是日子越来越好的原因,娘不显老,心态也好的很,对新的东西吸收的快,更乐意跟着我出去玩。我说,娘,我出差,跟我去上海玩吧,娘说,好呀,只要你老子同意就行。娘受我父亲—辈子气,不是怕,而是让着他。比如看电视,父亲非常霸道,总看什么《英雄儿女》呀,《地道战》之类的战争片,看就看呗,还常常看着就睡了。奇怪,娘刚把台调成《红楼梦》,他就醒了,不调回去,他就吼。工作后,父亲对我的态度变了,从不发脾气,甚至有几份蹙。我带娘走,父亲是不会阻挠的。每次,娘总能顺利而又兴奋地随我出门远行。
娘是个俭朴的人,平时,她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用。你要给他买什么东西,她总不要。硬买下给她,她气,说我花钱手太大。可是,出门在外,见我大把花钱,她从不阻拦。娘,个子高,一米七0的样子,人又生的白净,骨子里透着书香熏染出来的气息,是个不笑不开口说话的慈善的人。我乐意和娘一起出行,有娘在身旁,我长脸。娘说,穷家富路,苦处挣钱乐处用,花钱抠抠索索的,会让人看不起的,人呀,眼睛势利的很。接着,娘便会同我讲过去,讲外婆家曾经的辉煌,讲她当年和同学们来上海时的情形,讲现在的娘家称下的一个姐姐和弟弟。说起他们,娘免不了要难过一番。是的,老陈家多大的家业,说没了就没了。大姨,曾是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丈夫战死后,她又被国军的散兵抢了个精光,在自己都难以活命的情况下,她不得不把刚满周岁,还吃着奶的女儿,偷偷地丢在解放军部队门口,自己一路讨饭,从浙江往家里来,没曾想来到家,解放了,家也破了。后来,出于无赖,她给一个死了老婆带着两个孩子的,老实而又贫穷的农村汉子做了填房。老舅更惨,堂堂的陈家少爷,南京国立中学的毕业生,相貌堂堂的一个男人,因为背着地主成份,一有运动就挨批斗,连老婆都娶不到,至今还孤独一人,生活在乡村。我说,娘,别难过,有我们呢,现在,大姨的日子,还能说得过去,老舅也能自食其力,等将来他们老了,我们兄弟们会照看他们的,娘,你放心。娘笑,她说,不说了不说了,都是命。如今,娘有你们这些懂事争气的儿女,娘也知足了。现在,娘对你们什么想法都没有,不求富,不怕穷,只盼着你们一个个平平安安的成家成人。儿啊,家,就象似一只木水桶,娘呢,就象水桶箍,将你们兄弟们一个个紧紧连在一起的,娘在,家就在,无论你们走多远,心里也有个盼头,多个念想。儿啊,好好弄,凡事别做过了头,娘这半辈子过的苦,现在好了,娘便想多活些日子,跟着你们享享福。我笑,我说,娘,只要有机会,我出门一定带上你,满世界地走。娘笑了,笑的特舒心。
只可惜,我带娘去的地方太少太少。
娘最高兴地是过年,孩子们都来家了。娘系着围裙,弄弄这个,洗洗那个,一会儿指派谁谁去贴上门对子窗户花呀,一会儿提醒谁们去烧火纸呀!我说,我们连爷爷的坟都不知道在那里,烧什么呀,娘笑,娘说,小心,你老子听见了又不高兴。坟不坟的无所畏,这是规矩,是人都有祖宗的,你们就去三岔路口烧纸,是个意思,大鬼小鬼都过年,保佑全家都平安就行。娘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忙碌着,高兴时还会轻声地哼唱几声,把家拾弄得温温暖暖,把一个年过得有滋有味。
年夜饭上来了,摆满了桌子,丰盛而又可口。有两道菜是娘最讲究的,一个是鱼,一个是豆腐阆肉圆子。圆子是团圆,鱼是连年有余,鱼是不准吃的,一定要余,余到初五过小年,放完送年炮,才让动筷子。一家三代十几口人围坐着,小孩子们忍不住,上手就抓着吃,娘见了不允许,娘说,放炮去呀,放完炮开能开席的。于是,年,在一串鞭炮的脆响声中来了。
吃完饭,拜年开始,头一定是要磕的。从大哥大嫂开始,按顺序来,娘和父亲端坐着,守侯着孩子们的祝福。压岁钱是少不了的,每个人都有一份,多少不计,一律用红纸包着,磕完头,说了几许祝福话,娘便发红包。我们大小十几个人一路磕下去,引来一片欢声笑语。望着自己的儿孙们,娘的眼睛里满是喜悦,满是说不尽的慈爱。有人喊,春节联欢会开始了。于是,一家人就围坐在电视机前,边看晚会边守岁。娘不看,叫她,她说,会重播的。她忙着拾碗洗刷,又一遍遍地给我们端上糖果,花生,水果,还有娘自己做的炒米糖。零点不到,娘就催着让去放开门炮,娘说,多放,开门炮越响亮,开年的日子就会过的红火。放完炮,娘就催我们去睡一会儿,舅为大,初一我们要给舅舅拜年去。娘又准备好礼品,弟弟参军,我们家是军属,父亲又是老干部,每年初一,旱船队要来拜年的。
拜年时,一只扭动的花彩旱船,一个乐队,七八个扮上的俏姑娘伴舞,一个划船老翁,一个嘻笑的领唱,见风采柳地唱着吉利话,众人跟着合,一曲终了,主家便在船头放上礼品,一般不少于四样,香烟,云片糕等等。主家放几次,旱船就得唱几次,扭几次,再累,也不兴走的。什么时侯主家不再往船头放礼品,礼节性地放响一挂鞭炮,曰:送船,旱船队才能离开,去另一家。娘十分在意这份荣誉,礼品往往准备的足足的,娘总想旱船能在自家门前多扭一会儿,娘是个要面子的人,娘认为,旱船上门,那是全家的光彩。旱船走了,亲戚上门了,初一外甥,初二女婿,初三侄子……年,就在一天天的客来客往中度过着的。
今年,是我十六年来,第一次没回家乡去过年。
我的父亲,在四年前去逝了,父母不在了,再回去过年,心里少了几许热情。再说,我己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我们要学会自己过年。于是,我和妻子忙着过年,妻子将家里装扮的喜庆而又热烈。我也亲自下橱,学做娘常做的豆腐阆肉圆子。忙活了半天,端上桌,儿子说,老爸做的不叫圆子,应该叫豆腐煮肉沫汤。贴春联,放炮,渴酒,磕头,给儿子女儿压岁钱。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心里少些什么,人少?冷清?都这样啊?更何况,我还是四口之家。妻子和孩子们去看晚会,我没心情看,蓦地,我想起一句话:家有老,是个宝。我知道,我想娘了。于是,我独自饮酒。
妻子知道我的心思,她说,少喝点,别喝醉了。儿子也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跑过来用红酒陪着我喝,儿子虽然一米八0的个子,毕竞才十六岁,本不该让他喝酒的,然而,我却放纵了他。我和儿子边喝边说着关于故乡,家,娘,过年……不知不觉地,我俩都喝醉了。
大年夜,梦见了娘,这也是我十六岁来第一次在梦里见到娘,娘坐在我身边,笑盈盈地望着我,就是不说话。我说,娘,我渴呀,想喝水。娘还是不说话,用手摸了摸我的头,我忽然惊醒。抬眼,是妻子,正端着水,她说,来,喝点水再睡。喝完水,我完全醒了。唉,真想回到刚才的梦里找我的娘去啊,可是,我睡意全无。
娘,过年了,儿想您。
(4600字)
2009年1月26日正月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