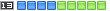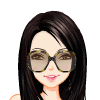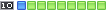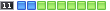我和黛 麗 校 長
蕭 振
黛麗是成人學校的校長﹐我和她交往有點像不打不相識……
首遇黛麗,
第一回合?
剛移民美國﹐我報名參加一個在成人學校由政府資助的電腦班。好幾百人報名﹐只錄取了三十幾人﹐分兩班。我有幸被錄取了。我們班連我在內只有兩個老中﹐其他是白人﹑黑人﹑墨西哥人﹑越南人。
開學典禮﹐一個高大壯實﹑年約四十歲的婦女來講話。五呎七﹑八的身高﹐皮膚略帶咖啡色﹐頭髮棕色捲曲﹐胖嘟嘟的圓臉﹐大大的眼睛﹐高聳的鼻子﹐棱角分明的肉感的嘴唇﹐珠光閃閃的耳鐶綴在兩個耳垂上﹐黑色的文員套裙在她身上更顯出她的丰滿﹑利索﹑精明。
主持人介紹﹐她是校長黛麗。
黛麗講話後﹐說讓我們也上臺講講﹐說什麼都可以。
黛麗點的第一個人是老墨婦女。她講了她的家庭孩子。
我的第六感官告訴我﹐下一個點的很可能是我。說什麼呢﹖一不能俗套﹐二不能重複說家庭﹐三是自己有限的英文能表達……
果然﹐黛麗第二個點的就是我﹗
我說﹕
“我說一個笑話。有一個人很喜歡喝酒﹐(臺下有個黑人同學附和﹐我也是。)我有時候也是。有一次他喝多了﹐走路(我不會說英文的歪歪倒倒﹐表演了醉拳東歪西倒的步態。會場氣氛活躍。)摔倒了。(你摔呀﹗摔給我們看看﹐台下喊。)你上來摔吧。(我指著喊話的人說。哄堂大笑。)手裡拿的一瓶酒也摔破了﹐滿手是血。這人還說﹐真幸運﹐流的是血不是酒。(掌聲﹐笑聲。) ”
掌聲和笑聲已經說明講話內容有新意。話不多﹐英文基本夠用﹐一點點不夠的地方配合肢體語言﹐又說又演﹐生動活潑﹐皆大歡喜。
我躊躇滿志地離開講臺。但就在我走出講臺的時候﹐黛麗校長從最靠邊的座位附近急急忙忙走過來叫我等一下。我淡定中不無狐疑又回到講臺邊。黛麗校長雙手背後﹐一本正經地問﹐“從哪裡來美國﹐以前做什麼工作﹖”我一一如實回答。得知我學醫﹐她眼睛露出一種懷疑和好奇的眼光又問﹐“有沒有做屍體解剖﹖怕不怕﹖”臺下的同學也交頭接耳﹐興趣盎然。我是誰﹖﹗我回答得斬釘截鐵﹐我就答四字﹐ “當然﹗不怕﹗”問答完了﹐黛麗校長讓我回座位。
當時﹐我沒意識到這是我和黛麗交手的第一個回合﹐只當作是偶然巧合的尋常事情。
课堂抽查,
第二回合。
幾天後﹐黛麗來講社会課。她一開口便滔滔不絕﹐上至政府部門﹐下至黎民百姓。從上流社會到草根階層。加上恰到好處的肢體語言﹐講的是生動活潑﹐聽的是饒有興趣。我一邊竭力抓住她的每句話﹐一邊在仔細端詳她。隨著講話內容的變化﹐她的面部表情像走馬燈一樣地變﹐時而莊重像石雕﹐時而高興得像朵花…… 我想﹐這個女人不簡單。聽著﹑看著﹑想著﹐她突然大步走到我座位前面﹐石雕般莊重的脸色對著我﹐說她知道我聽明白她的話。
我明白她有意無意地在留意我了。也許懷疑我憑什麼進到這個班﹖
快下課了﹐她再次走到我座位前面﹐胖嘟嘟的臉顯得殭硬﹐兩只手交叉抱在胸前﹐她讓我寫幾句話概括她講課的中心意思﹐但別人都不用寫。
我心理有點不平衡﹐明顯地感到不公﹗但又想﹐或者是關照呢﹖到底是哪一種﹖我至今沒去搞清楚。幸虧英文我還懂一點﹐加上多年的歷練﹐我很快寫了兩﹑三句話概括出她講話的中心。
我不管她還在講臺上講得天花亂墜﹐我站起來離開座位﹐徑直就走到她面前遞上我寫的東西。因為自以為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不卑不亢地看著她。
她臉色依然殭硬﹐她接過來溜了一眼﹐語氣平淡﹑聲音不大不小地說﹐“See! This guy.”
是褒﹖是貶﹖是中性﹖我也至今沒去搞清楚。
她隨後一句下課﹐便結束了我們的第二個回合的交手。
測驗過關﹐
第三回合。
以後一段日子﹐相安無事。
黛麗也來得不多。課間休息﹐我在校園教同學打太極拳。她偶而路過﹐互相打招呼﹑Say Hi﹐她就走過去了。
不久﹐進行一次對個人的綜合素質測驗。
每道題都有不同的時間完成﹐長則一分鐘﹐短則二﹑三十秒。每道題老師說開始做則開始做﹐說停則停。也就經常聽到“開始﹗”“停﹗”“開始﹗”“停﹗”……
雖則我對此測驗不以為然﹐但也入鄉隨俗﹐專注地做著。只是常覺得身後有黛麗的眼睛﹐但也不容我多想﹐因為這邊廂不時喊“開始 ” ﹑“停” ……一心不能二用。
最後一道題是滿滿一頁的豎著下來的如同鏈條般﹑細細窄窄的長方格﹐讓你在每個方格裡填上線﹐線短了扣分﹐線長了也扣分。看你在規定時間能填多少。
一聲令下﹐“開始﹗”我照樣豎著下來唰唰的填﹐馬上覺得不順手﹐不夠快。立刻不管三七二十一﹐掉轉試卷變成打橫填﹐如此一來便快多了。此時﹐我眼尾感覺到黛麗就在我身旁。我沒工夫看她﹐我不知道她對此作何感想﹐反正不是作弊。我後來一直都沒問她。
最後一次測驗在大教室﹐和別的班一起近百人。排隊進去後﹐學員都坐得相隔很遠。好幾個監考老師巡視﹐一下沒看到黛麗。我忘記考什麼了﹐只記得其中有些數學的內容。這回沒覺得黛麗出現在我身後。我不知道她去了沒有﹖我是第一個交卷。我想她會知道。
這第三回合確切地說不算交手﹐沒有丁點火藥味。有前兩回的鋪墊﹐第三回合對黛麗來講﹐我想是資格驗證。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三關過後﹐在路上碰到黛麗﹐就不是僅僅打招呼﹑ Say Hi了﹐她常常會停下來﹐兩手自然垂下﹐兩個嘴角往上一翹﹐嘴巴就綻開了充滿陽光的笑容﹐還常常和我聊幾句。
開始﹐我還是保持國人習慣﹐講話不緊緊盯住她的眼睛。謙謙君子之態。黛麗卻老實不客氣地對我說﹐和她說話就要一直盯著她的眼睛。
恭敬不如從命。自此我和她說話﹐我的眼睛就盯著她的眼睛﹐更推而廣之到所有的老外。在西方國家講謙受益﹐好比對牛彈琴﹐讓人笑話的不是牛﹐仍然是彈琴的人。
電腦班的學習差不多結束了﹐黛麗有一次把她家的地址﹑電話寫在黑板上﹐說一是相信大家﹐二是歡迎大家找她。我想﹐既然和她的認識像不打不相識﹐我也敬重她的人品和學識﹐何不交個朋友﹖我打電話給她了﹐問她星期天有空去飲茶嗎﹖她欣然受邀﹐口氣有點驚喜﹐問我要穿什麼衣服﹖我說隨她喜歡。
哪天﹐她滿臉都是笑﹐像春風吹化了冰。她穿了件連衣裙﹐雖無玉樹臨風感覺﹐也還賞心悅目﹑大方得體。
“焗叉燒包 ”是她最愛的點心。
我欣賞她用刀叉分離鳳爪皮骨的專注樣子。我也鄭重其事地給她示範老中吃鳳爪的嘬法。她試了﹐但看得出來她還是習慣動刀動叉。
禮尚往來﹐不久她請我吃意大利餐。
一來二往﹐大家了解更多了﹐我請她到家裡作客。
一個夏日的黃昏。她穿一襲白底紫色碎花連衣裙﹐莊重而不失嫵媚。我們坐在客廳聊天﹐後來談到醫院的問題﹐她說上網查查。我的電腦在書房﹐便請她到書房。
窗外﹐晚霞燒紅了天。落日的余暉投灑在她端坐的身體上。白底連衣裙幻化成金黃色在她身上更顯得貴氣﹑華麗。我為這一情景陶醉。可惜自己不是畫家﹐否則畫下來絕對是一幅有震撼力的﹑能攫住人心的好畫。
我自顧欣賞。她見我無聲無息﹐回頭看我。我注意到她一雙大眼睛裡面﹐淡褐色的瞳仁像海一樣深邃﹐蘊含著智慧﹑真誠和信任。
樂人之吉﹐慈心于物。我們就這樣成了君子之交。雖然還是稱呼她叫黛麗﹐現在這個黛麗已經不是以前哪個黛麗了。
黛麗也請我到她家作客。我開車轉了幾圈﹐路名都對但門牌號數不對。我無奈地在路邊借人家的電話打到她家。她馬上說她來帶我。她開著車很快到了。就這樣﹐我開車跟著她的車子到她家。告別的時候﹐她又特意開車再帶我在路上走兩次。真的是仁至義盡。
我第一次在她家游泳﹐把眼鏡掉到水深的池底。我沒有眼鏡兩眼昏花﹐幾次潛水都找不到。黛麗急忙叫她兒子下水幫忙。她兒子正在脫長褲﹐這邊廂我想不能太麻煩人家﹐更不能丟人﹐猛又潛下去﹐這一回終於找到了眼鏡﹐掙回點面子。
黛麗還幫我修改一份商業計劃。是一份和一間硅谷的生化公司合作的計劃書。我寫了英文草稿﹐總覺得行文造句不夠美國﹐因此打電話約黛麗飲茶﹐請她修改文稿。她中肯地提了幾條建議﹐很快就把修改稿印給我。她的文采令我佩服。她幫我修改草稿的這一件小事始終印在我腦子裡。我們是亦師亦友。
我也幫過她。她患了濕疹﹐懊惱不已。我建議她用中西醫結合辦法治療﹐既服西藥﹐又服中藥。結果服藥一段時間﹐她痊癒了。
一個星期天﹐她開車載我和我太太去海濱玩。我們一路談笑風生﹐快樂的心情就象車外的麗日藍天﹐燦爛陽光。沙灘上﹐我們像年輕人一樣迎著涌上沙灘的海浪跳來跳去﹐全然不顧捲起的褲腳都濕掉了。忽然﹐黛麗笑嘻嘻地瞇著眼睛狡黠地問我﹐“振﹐你還有酒鬼的笑話嗎﹖”“當然。” 我太太也知道當初的故事﹐叫我再講一個給黛麗聽。
我說﹕
“還是上次說的哪個酒鬼。” 我故意不改動人物。
“他的手沒事了吧﹖﹗”黛麗明知故問。我不管不顧繼續說﹐“他在希爾頓酒店又喝酒喝到东倒西歪,在酒店大堂門口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機说到希爾頓酒店。司機纳闷地回答说這裡就是希爾頓酒店。‘真的嗎﹖’ ‘沒錯﹗我不會騙你。’ 於是﹐酒鬼一邊從口袋裡掏出二十圓鈔票給司機﹐一邊說﹐‘好極了﹐這是給你的錢﹐不過下次不要開得這樣快了。’ ”
掌聲﹑笑聲。黛麗和我太太邊鼓掌邊笑得前仰後合﹐最後倆人笑得抱作一團﹐一不小心都笑倒在沙灘上﹐幸好沒弄濕衣服。都是酒鬼的笑話﹐前後卻出現兩個結果。
不久﹐我女兒出嫁﹐黛麗很快就寄回來了她一家要參加婚禮和婚宴的回帖。
婚禮哪天﹐她穿著棗紅色的套裙﹐棗紅色的半高跟鞋﹐猩紅色的耳墜在兩隻耳朵下生動地搖幌。一身喜氣洋洋。她比我們更早到了教堂。她緊緊擁抱了我太太和我﹐激動得眼眶都濕潤了﹐倒像是她在嫁女兒。我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們是不打不相識的朋友﹐更因為我們的朋友交往是心與心的交往﹐沒有世俗的利益關係摻雜。君子淡以親。
教堂的管风琴奏起了雄渾撼人的結婚進行曲﹐我女兒挽著我的手臂款款步入教堂的時候﹐音樂和心靈的碰撞﹐聖潔和世俗的交融﹐使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上天給了我這一切﹐包括認識黛麗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