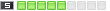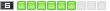孔子删诗说考辨及新证
2012-05-23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刘生良
内容提要:“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一大公案。纵观历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逸诗的多少、《左传》季札观乐的记载、《论语》所言之“诗三百”、司马迁所言之“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正乐与删诗及孔子有无权力删诗五个问题上。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并结合最近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所提供的新证,不难看出否定论者的种种理由都不能成立,“孔子删诗说”不容置疑和否认。
The "remark of Confucius's deleting The Book of Poetry"remains a well-known disputable cas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Poetry.Adiachronic view reveals that all disputes spotlight the following five issues,namely,how many poems were los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in the part of Ji Zha inspecting music in"Zuo's Chronicles","300 poems in all"as was mentioned in The Analects,"deleting the duplications and preserving the sound advocating propriety"as was remarked by Sima Qian,normalizing music,deleting The Book of Poetry and whether Confucius was entitled to do so.Through a careful investig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and according to the fresh evidences offered in the recently revised edition of "Confucius's Poetics"on Bamboo Slips from the Kingdom of Chu in the Warring Kingdom Period in stock in Shanghai Museum,it is clear enough that the"remark of Confucius's deleting The Book of Poetry"admits no suspicion and denial and that the miscellaneous reasons offered by those deniers are all groundless.
关键词:孔子删诗说;竹书《孔子诗论》;逸诗;诗三百 remark of Confucius's deleting The Book of Poetry;Confucius's Poetics on Bamboo Slips;lost poems;300 poems in all
--------------------------------------------------------------------------------
孔子对《诗》的整理编订,史称“孔子删诗说”。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段话,对孔子编诗的背景、原则、断限、方法及有关体例的调整均作了说明。自汉至隋,历代学者及有关史志对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和解释说明。及至唐初,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诗谱序疏》始以“《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从而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并不否认“《诗三百》者,孔子定之”。然此说一出,即为后来否定“孔子删诗说”者开了个头。
纵观历来关于“孔子删诗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逸诗的多少、《左传》中季札观乐的记载、《论语》所言之“诗三百”、司马迁所言之“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正乐与删诗及孔子有无权利删诗几个问题上。本文兹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结合最近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所提供的新证,分别辨证如下:
一、关于逸诗多少的问题
否定论者认为,从先秦古籍引诗情况看来,见于今本《诗经》者多,属于逸诗者少,因而司马迁“古诗三千余篇”之说不可信,“孔子删诗说”也难以成立。此说由孔颖达发难,赵翼等人推波助澜,(注:赵翼《陔余丛考》卷2通过对《左传》《国语》引诗情况的全面统计,说明逸诗“不及删存诗的二三十分之一”,认为“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成为否定论者的首张王牌。对此,欧阳修、卢格早就论证了“古诗三千”的可能性,以反驳孔颖达的疑难。(注:欧阳修《诗本义》卷16云:“案迁说然也。……以郑康成《诗谱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此观之,何啻三千?”朱彝尊《经义考》卷98引卢格云:“西周盛时,环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国,使各陈一诗,亦千八百篇矣。”)马国翰在《目耕帖》卷23中还将各种古籍所引逸诗进行辑佚,共辑逸诗104首,以回击赵翼所谓“逸诗不及删存诗的二三十分之一”之说。今世学人多认为以逸诗少来判断古诗无三千之数和孔子未曾删诗,是很不科学的;被删汰的逸诗质量不高,自然引用者少;逸诗的存在就已证明古诗数量大和孔子删过诗。[1]而最令人服膺的,是台湾陈新雄先生的考辨。他联系《孔子世家》上下文“前后观之”,指出“司马迁明言,孔子之时,已经是‘诗书缺’,古诗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时诗已有缺,则自无三千余篇。前人读《史记·孔子世家》之文,多未前后贯连,故有删诗十去九之论”[2](P328-329)。此诚乃发前人未发之创获。至此,关于“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司马迁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之类的疑惑,则涣然冰释矣。仔细分析《孔子世家》有关记述,作者是在叙述孔子正礼乐、删《诗》《书》之前,先有个“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之总背景的介绍,至叙及删《诗》时,因上文已说明《诗》已缺,故在“古者《诗》三千余篇”之下,明显承前省略了“此时已缺”之语。这与太史公先总后分的叙史笔法和简练原则颇有关系。读此史文,必须前后“互见”,方能准确把握史公原意,否则就会产生误解。显而易见,司马迁关于孔子删诗的记述,根本没有十去其九之意,尽管行文有所“疏略”。只怪孔颖达读书不察,误解史文,以致谬说流传,贻害千载,误人匪浅。
以上是就现存历史文献将逸诗问题基本辨明,同时,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也在这一问题上为司马迁的记载提供了证据。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和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均发现逸诗,特别是在最近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似乎发现了较多的逸诗。据马承源先生考释,这次新发现的29枚孔子论诗竹简中,记孔子授诗共涉及诗59篇,有1/10多是今本《诗经》中没有的,新发现的逸诗是《可斯》、《河水》等7篇[3](P160-161)。对此,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并非逸诗,“所谓‘逸诗’篇名,今本都有对应”[4]。倘如此,那就自不必说了。在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姑且作为逸诗看待,那么这些逸诗的发现,则更说明孔子当时所见到的《诗》比今本多得多,从而印证了司马迁《孔子世家》有关记载的正确性。发现的逸诗越多,越能证明古诗数量大和孔子删过诗,越能证明司马迁所言之可信和不容置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某些记者同志在其报道和文章中,却以孔子论诗竹简中新发现的几首逸诗为据,竟轻率断言“孔子当年没有删过诗”、“孔子并未删过诗”。(注:见《文汇报》2000年8月16日头版《上海战国竹简解密》的报道,2000年8月26日12版《孔子有没有删过〈诗〉》一文,《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2月22日头版《战国竹简改写先秦学术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首册出版》的报导。《解放日报》2000年8月25日、《新民晚报》2000年8月26日的报导性文章也有类似说法。)按照他们的逻辑,似乎一旦发现逸诗,就可证明孔子没有删诗,那么,自马王堆帛书发现逸诗以来,“删诗说”早该被否定了,但是为什么学界不但没有否定反而越来越趋向肯定呢?这显然是他们弄错了,搞反了。也许他们会说,这次发现的逸诗不是一般的引诗,而是孔子亲自讲论的。殊不知早在《论语》中,孔子就曾讲论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和“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两首逸诗。竹书《孔子论诗》中这些逸诗和《论语》中的逸诗一样,只会给“删诗说”以有力支持,给怀疑、否定论者以沉重打击。这些同志对《诗经》和《诗经》研究缺乏了解,其草率、武断、肤浅和错误之说,断不可取。
二、关于季札观乐的问题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于此年(公元前544年)适鲁观乐,鲁乐师所奏乐曲之次第,即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孔子当时只有8岁,尚无力删诗。这是否定论者最得力的证据。刘克庄、苏天爵、崔述、朱彝尊、魏源以至今之否定论者都以此认为孔子绝对不可能删诗。但是肯定删诗说者对此则极力予以辩驳,有的据《周礼·春官·太师》贾公彦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传家据已定录之”,认为“传者从后序其事,则据孔子定之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5]。有的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云“《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认为季札观乐之记载是“从后傅合”而成[6]。有的认为是“春秋后人所捏造在成书时插入的”[7]。有的认为孔子在诗的分类编排上可能是依照季札所观周乐的旧例进行编选[8]。有的认为周乐虽是“诗三百”的母体,但观乐毕竟不同于观诗,这与孔子删诗不矛盾。这些考辨都不无道理。
笔者曾受郑樵《六经奥论·删诗辨》所云诗三百五篇“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的启发,认为季札观乐为鲁太师所奏,孔子编诗以鲁太师所藏古诗为蓝本,二者同出一源,岂能不基本相同?因而以季札观乐否定孔子删诗,显然不足为据。[9]现在据上海新出版的竹书《孔子诗论》,诗的顺序不是风、雅、颂,而是讼(颂)、夏(雅)、风,倒了个头[3](P131-139)。这一新发现已清楚地说明孔子当初讲诗时《诗》的编次与鲁太师当年奏乐之次第根本不同,也说明鲁太师所存古诗之编次与其奏乐之次第是显然有别的两回事。既然如此,则“季札观乐”这一否定论者所谓最得力的证据,就显得毫无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诗经》的次序为何与竹书《孔子诗论》不同呢?笔者曾对古诗的收集和早期整理作过考察,[9]关于古诗的收集,我在传统的“献诗”、“采诗”二说之外,又提出“作诗”一说,因为在我看来,《诗经》中的宗庙祭歌,不可能是通过“采”或“献”得来的,而应是由专司此职的文人乐官亲自创作的。因此我认为古诗是通过采诗、献诗、作诗三条途径收集起来的,这大体上相当于后来风、雅、颂三部分的分类。关于古诗的整理编辑,我认为其最初大概是由周初的乐官太师之属将他们所作的宗庙祭歌、公卿列士所献雅诗以及从列国和民间采集来的土风歌谣汇集起来,略加编次,称之为《诗》。其编排顺序,我隐隐觉得应以颂、雅、风相次(竹书《孔子诗论》的编次完全印证了我这一想法的正确性)。随着所采所献以及所作诗篇的不断增加,历代乐官太师及其僚属当随时将其归类补充编排。至孔子之时,礼崩乐坏,《诗》《书》残缺,但《诗》的编次大致犹存。孔子对《诗》的整编,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大概在中年设教时,亦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时,应教学之需先作了初步整理,晚年又曾进行过调整编定和正乐的工作。竹简所记乃孔子前期编诗、教诗之顺序,故仍以颂、雅、风之旧例相次。至于今本《诗经》的次序为何与之不同,这很可能是孔子晚年“自卫反鲁”,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调整所致,或许因为后来颂诗中新补入了《鲁颂》、《商颂》,似乎不宜再以颂诗为首,所以孔子把它和风诗的位置调换了一下。
三、《论语》所言“诗三百”的问题
否定论者认为,《论语》不止一次说到“诗三百”,说明孔子所见之《诗》即为三百篇,因而孔子没有删诗。如叶适《学习记言》卷6云:“《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自定者言之。然则《诗》固不因孔氏而后删矣。”朱彝尊《经义考》卷98云:“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属删后之言。……窃疑当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余篇而已。”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三章云:“孔子四十五岁已讲学,他向来教人都用《诗》。他自卫反鲁以前,用三千篇教人呢,还是三百篇?孔子常说‘诗三百’,‘诵诗三百’,玩其词义,在反鲁之前就是用三百篇,并不是反鲁以后才从古诗里选出三百篇。”但是据我看来,《论语》两言“诗三百”,一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则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细玩其词义语气,似都指其所编订之诗而言,前者是对其思想内容颇为满意的自评,后者是教导弟子学习《诗三百》,不能只会诵读,要学以致用,这都好像是在讲授《诗三百》的过程中说的。其“诗三百”是概数,起初所收篇目有可能比今本略多一些,盖至后来一一“弦歌之”即再次整理、最后修订时似乎还有所淘汰,才形成305篇之定本的。孔子编诗的目的,一是为了“备王道,成六艺”,克己复礼;二是为了教学,即所谓“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既已用于教学,就说明已是初步编成之《诗》无疑。这显然是其中年设教时就完成的,绝不是69岁“自卫反鲁”后才进行的。“反鲁”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当是指孔子对《诗三百》进行正乐和调整的最后一次修订而言。今人已经指出:“诗三百”之说,在孔子之前不见于史籍,而首次出现在《论语》记述的孔子言行中,后来诸子提及“诗三百”者,也莫不与儒家有关,以此而断,惟孔子编选《诗经》方有可能。[10]对此我深表赞同。的确,“《诗三百》”之称始出于孔子之口,后来墨子抨击儒家在服丧期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做法,其“《诗三百》”显然指孔子编定的《诗三百》。由此可见,《诗三百》是孔子对他所编之诗定的名,也就是说,《诗三百》是由孔子整理定名的。
四、司马迁所言“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问题
否定论者认为,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与事实不合,因而孔子不可能删诗。如崔述《洙泗信考录》、朱彝尊《诗论》认为许多不合礼义,甚至孔子扬言要删掉的“淫诗”竟存于《诗经》,而一些合乎礼义,孔子曾极力赞赏的诗却不见于《诗经》,可见史传失实,孔子未尝删诗。张西堂又说:“任何乐师都可以将重复的诗篇去掉,岂能等到孔子才去其重?”[11]这是关于孔子删诗原则、标准之细节问题的责难,前人已作了一定的解释和辩驳。关于“淫诗”问题,朱熹云:“郑卫之音,便是今邶、?{、郑、卫之诗,多道淫乱,故曰‘郑声淫’。圣人存之,欲以知其风俗以示戒,所谓‘可以观’者也。”因此,他对所谓24首“淫诗”也照样予以保留。顾起元则主张将郑声与郑诗分开,认为“言‘郑声淫’”者,谓郑国作乐之声过于淫,非谓郑诗?皆淫也”。今人多认为“郑声淫”只是孔子对郑声的评论,并不是其删诗的标准。刘操南先生指出:“孔子删诗,司马迁只说‘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两条,并未提出‘贞淫’为标准。周时采诗,‘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贞淫’都可入诗。孔子曾云:‘诗可以观’。‘俗有淳漓,词有正变’,正可以观,从而移风易俗。孔子不仕,《诗》授弟子,义有美刺,作《春秋》,书有褒贬,正反皆可教育。岂必攻乎一端,执一而论。以贞淫为标准删诗,自是后儒臆说,不足以乱孔子删诗之说。”[12]此说颇为中肯。关于“重复”问题,郭绍虞根据“天子听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的记载,认为就这种制度而言,那么照例的应制诗当然可以重复,而所采之诗一定比应制诗多得多,民间歌谣中的重复现象极为普遍,被孔子删掉的可能就是这些重复的诗。[13]郭先生此说很有道理,即以近年各地流行的一些新民谣来看,多是大同小异,如果收集起来,肯定重复的很多。但古诗中的重复是不是乐师早已去掉,轮不到孔子呢?蒋善国《三百篇演论》说:“即以现在的三百五篇诗看,其中有很多重名的,可见孔子时所存于国史的诗,重复的必然比现存的更多。”由此看来,乐师们整理保存古诗,并不一定“去重”,即使偶尔为之,留下的重复仍然很多。“去其重”的工作便历史地落到了孔子肩上。
细读史文,我对“取可施于礼义”还有新的认识。在我看来,所谓“去其重”,就是去掉重复、多余的诗篇,那么与此相关的“取可施于礼义”,实即取其篇章相对完整、可用于礼乐演唱者,舍弃那些已不能用于礼乐演唱的残章断句之意。请注意,史文是“可施于礼义”,而不是“符合礼义”。施者,用也。“施于礼义”正即古人收诗用于礼乐演唱之本旨,与内容之是否符合礼义无涉。因为古人收诗,“贞淫”皆可入诗,都可以“观”,都可施于礼义,只要篇章完整,能够演唱。季札观乐,郑卫之诗不就是被堂而皇之地“施于礼义”吗?而孔子之时那些严重残缺、无法演唱的零章断句,即使内容再符合礼义,也不可“施于礼义”,因而必然为孔子所删汰。因此,去其重复,舍其残缺,乃司马迁关于孔子删诗之本意。这与下文“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紧相承接、照应,顺理成章,可以互证。前人曾云:“三百五篇之外,单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肄业虽不妨及之,要无与于弦歌之用。”[12]也是最有力的佐证。其起初编选时较多删汰的篇目已难详知,以可能在最后修订时少量淘汰的篇目为例来说,《论语》中孔子所论及的两首逸诗之所以最终被排除在《诗三百》之外,“巧笑倩兮”一篇概因与《卫风·硕人》重复(或许还属残章)而被删,“唐棣之华”一篇很可能因残缺不全、要无用于弦歌之用而不收。这次发现的竹书《孔子诗论》中的所谓7篇逸诗最终未被孔子收编,或因重复,或因残缺,或另有原因,尚待深考。由此看来,孔子删诗并非以礼义为取舍标准,更非像“刽子手”一样随意乱删,而是就当时已缺之《诗》,依自己所定的时限,对篇章完整且不重复者,能取则取,全都保留了下来。这也为后世的古籍整理树立了榜样。那么,所谓“为何淫诗不见删而合于礼义的逸诗不见存”云云,实属不求甚解、不得要旨的无谓之谈。不仅如此,欧阳修所谓删篇删章删句删字之说,也是隔靴搔痒、郢书燕说的臆解。“取可施于礼义”之本意既昭然揭明,则千载以来在此问题上的所有疑惑和责难,皆可以休矣!
五、正乐与删诗及孔子有无权力删诗的问题
否定论者认为,孔子自己只说“正乐”,没说“删诗”;再者如朱彝尊《经义考》卷98所说,孔子无权无位,“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此说更是站不住脚。以常理而论,诗歌本是诗与乐的结合体,岂有正乐而不及于诗者?《论语·子罕》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正”自是正乐,那么“《雅》、《颂》各得其所”就是对诗进行删补、整理的最明白不过的说明了。沈心芜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后曾指出:“‘乐正’和‘雅颂各得其所’一同置于‘然后’之后,明明是把所得的结果平列起来的两件事,而绝不是有因果关系的一件事。‘自卫反鲁’那是说明时间;‘乐正’那是说明孔子曾经‘正乐’;‘雅颂各得其所’,那就对《诗》免不了有所删削、改编、补充。现存的《诗经》,没有《鲁风》、《宋风》,《鲁颂》本是风体,强要列入颂类;《商颂》托言正考父校于周太师,而作者是孔子之祖。这一切不都是删削、改编、增补后留下的明明白白的痕迹吗?”[6]沈先生这些分析,尤其是认为《鲁颂》、《商颂》为孔子后来改编增补,很有道理,我非常赞同。至于孔子有无权利删诗,更无需多辨。孔子虽无权无位,但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无冕之王、名副其实的文化王,即历史上所谓“素王”,当时有权有位者谁又有孔子那样高深的文化修养呢?整理《诗》、《书》的工作,舍孔子其谁欤?《孟子·离娄》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史记·儒林列传》云:“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在礼坏乐崩、文籍逸散、面临失传之危的情势下,毅然担当起时代重任,整理典籍,编著六艺,这样的记载遍见于先秦两汉的各种著作和文献。《诗》为六艺之首,孔子岂有不管之理?即使否定司马迁之“孔子删诗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孔子整编过《诗经》。如朱熹就认为“夫子不曾删诗,只是刊定而已”。又说:“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至孔子时已经散失;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从古至今,人们既然都相信孔子整理过《易》、《书》、《礼》、《乐》,也写过《春秋》,怎么能惟独不相信他整编过《诗》呢?这次发现的竹书《孔子诗论》,进一步证明孔子不仅是《诗》的权威整编者,而且是最早、最有权威的普及者和评论者。孔子设教,弟子三千,不管王朝列国之臣信与不信,从与不从,有众多弟子及后世儒家信而从之,这就足够了。
综上所述,否定“孔子删诗说”的种种理由都不能成立。司马迁关于孔子删诗的记述,虽在某些细节上不宜细究,或有待商讨,但在总体上是不容置疑的。正像《史记·屈原列传》尽管存在许多疑问和缺略,但屈原其人绝非太史公凭空杜撰一样,著于竹帛、彰于史册的“孔子删诗说”也绝非无据或出于误传,是完全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的。这次披露的竹书《孔子诗论》并没有为否定论者提供任何证据,而是从逸诗和编次等方面为进一步肯定“孔子删诗说”,宣告否定论无可挽回的失败和破产,从而彻底破译这一千古之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证。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并通过以上考辨与新证,可以看出,孔子经过前后两次整编,对原本“三千余篇”而当时已大量散佚残缺的古诗,以鲁太师所传为蓝本,参以当时所能见到的周室及齐、卫、宋、郑、陈、晋、楚等诸侯国的传本,根据自己所定的时限,进行去重舍残的整理删订,编成一部共有三百多首完整篇章、体系完备的新的诗歌总集,将其定名为《诗三百》,并一一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以便“施于礼义”,进而“备王道,成六艺”。太史公所载诚不诬邪!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采鲁”,收录了完整保留下来的全部周诗和部分商诗,后来又特意将商、鲁之诗改编、增补入颂诗,将原颂、雅、风的编序相应地调整为风、雅、颂,以体现其对周代文化的崇尚和对其先祖的怀念。他还有意识地确定了《风》、《小雅》、《大雅》、《颂》各部分的篇首,即《毛诗序》所谓“四始”,以寄寓其政治理想和美学思想。根据确定的时限和去重舍残的原则,孔子对当时存留之诗,能收录的都予收录,并非以个人好恶大刀阔斧地进行删削。对所收诗歌,除了参酌各种传本在文字、音韵上(原本已由周太师“比其音律”)进行必要的校补修订外,基本上保持原貌。虽然如此,但以《论语》和新发现的竹书《孔子诗论》的有关解说看,却都自成体系,与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合拍,因而孔子对《诗》的整编和解说,亦是对《诗》的一次文化整合,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理想文化体系。《诗经》的编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最后的编定者是孔子。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和中国诗学的一大贡献,绝不能轻易否定或抹煞,也根本否定或抹煞不了。“孔子删诗说”不容置疑和否认,理所当然地应予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王泽君.孔子删诗说辨惑[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2] 陈新雄.删诗问题之探讨[A].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 马承源.孔子诗论释文考释[A].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朱自奋.战国楚竹书整理出版引发学界“地震”[N].文汇读书周报,2002-01-18.
[5] 皮锡瑞.诗经通论[A].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6] 沈心芜.重审“孔子删诗”案[J].文学遗产(增总17辑),1991.
[7] 朱东润.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A].诗三百篇探故[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周通旦.论孔子删诗[J].哈尔滨师院学报,1964(2).
[9] 刘生良.孔子与《诗经》的整编[A].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10] 李欣复,吴传之.孔子编选《诗经》辨正[J].浙江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11] 张西堂.诗经的编订[A].诗经六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12] 刘操南.孔子删诗初探[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13] 郭绍虞.诗六义考辨[A].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03期 编辑:黄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