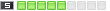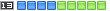董桥先生在《悼念没有书店的风景》一文里,追忆发生于纽约一间小破书房及英伦查令十字街84号之间的一段书缘佳话。索引为钟芳玲小姐写的《书店风景》,也屯在我上海的书箱里,过一阵子办海运,等拿到手,怕是年尾巴的事。董先生还特别回顾了查令十字同名电影,那也是我的收藏之一,隔几年就拿出来捋一遍。小说里,穷女作家一开始抱怨美国书贵,她说,I am a poor writer with an antiquarian taste in books and all the things I want are impossible to get over here except in very expensive rare editions, or in Barnes&Noble's grimy, marked-up shoolboy copies...我来新大陆第一天,便上网查询附近的大型书店,Barnes&Noble赫然在列,对一对汉芙小姐的暗讽,只要发笑。然而我都没有空走全Barnes&Noble哪怕一圈,一进门就被拖去童书档,只是对牢小巧硬皮的波特小姐发了一回痴,却根本无从评判一般文艺书籍装帧优劣。
此其一,董先生动不动就讲讲识藏旧书的别致经历。再有梁文道,有阵子介绍德国思想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后者尤爱旧书,将封尘至转手复开启,视作书籍的重生,与之相契者,便如友人萍聚,在命运轮转之中,也是读书人的幸运。我看多了,多少有点触动,不过买本雅明的书,仍然毕恭毕敬交足银子。
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想过买旧书的,也很少兴起版本收藏的妄念。起落于极度不安的生活,每每还要顾及身边的书,运走了怕别人照顾不周,留着又怕背不走,即或新书,已然深为所累。何况,我本来就不太在意风雅,什么版式、腰封、藏书邮,都没有兴趣钻研,也都敌不过一段隽秀文字。我却很怜惜那些埋没于大众视线以外的书,有的断了版,有的因书商跟风擦边畅销宝座,时不时是汩汩热意,细细谈它们的好处,我不太确定,我更在意那些书,还是背后难觅知己的人。
我也逛过旧书市,收获比如波特小姐一卷点点鼠,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乔斯坦.贾德的指环王之女。那可真考验眼力和耐力,还有抗扰力,尤其当老王喋喋不休表扬某本地图册时。以白给价拿到喜爱作者的簇新书籍,那样狂喜,绝对持久保鲜。
前一阵买新书的同时,终于一并订了几本旧书。一来,这里运费低廉,单本加足运费,也不过新书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价;其二,我觉得有些书恐怕也仅止于一面之缘,复习几率为零,拿本便宜的过过瘾就够了吧。
仍然还是用我熟悉的亚马逊。新书打一个包裹UPS来,旧书另发自不同书商,走平邮,慢几拍。结果每天晚上去查邮箱,我就像期盼圣诞奇迹的小孩子,惴惴不安,看到一本,便高兴得不得了,如果等空了,即用力按下心口凉意。原本一次累聚的喜悦,被推延拉长,而浓度不减,那守望的心情,和奔赴约会,似乎也没有太大分别,真是又甜蜜又痛苦。
又异于仿佛初生儿的新本,旧书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打开来,我似乎短暂切入另一人的世界,这重微妙及淡淡刺激,我也是从未品尝过。比如我特地买了万历十五年英文原版,发现原主人每隔几行就用鹅黄荧光笔标识重点,直至文末,书里还夹着一张大写READ彩色书签,粗体字母上绘有世界风情,上下古今,大约算西人对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揣摩。这位读者,想必曾经非常爱惜这本书吧。封底贴了几层条码,分属每一位二东家,这本书的命运也真够坎坷。
毛姆的戏院(Theatre),企鹅黑皮稍稍褪薄,有水渍痕,上任书主是不是把它带入洗衣房,一边等候一边读,取衣服时不小心倒扣在洗衣机顶上了?再有我现在每晚读一二篇,笑到打跌的艾柯散文带着鲑鱼去旅行(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一本我以为永远寄不来、姗姗而至的是!大臣(Yes, Minister),书很厚,脊背上折痕深刻,显然有人一径读到底,封面贴了一枚Clearance标志,那么就是说,这本几乎找不到新书的BBC出版,在那家好心书商手里,也是最末一本吧。
这次最大惊喜仍然是乔斯坦.贾德。我收到的嗨?那儿有人吗?(Hello? Is anybody there?)是本硬皮精装,封套压了透明膜,几乎全新,而我只花了不过五块。书来自华府某间地方图书馆,大约经手过多位读者,翻阅痕迹明显而并无任何污渍破损。我读到一半,忽然想起来,曾经一度找他一本书的法文版天上掉下来个小兄弟(Le petit frère tombe du ciel), 文名正好扣准这本书,估计法文取意译,英文直译,我一下子更觉得赚到了,好像同时读到两本惦念已久的好书。而这本书的插图呢,说不出的眼熟,看了几张,折回封页介绍,才明白图画作者借了小王子的构图。这便又喀喇弹开一重重记忆之门,供我一帧帧回顾读过的贾德,可不一律小王子布局吗?永远有一位充满好奇心、略略早熟的小朋友在那里不断发问,身旁的哲学讲师慈眉善目、海阔天空。苏菲的世界、纸牌的秘密、橙色女孩、在迷蒙的镜子里;白兔、魔术师的帽子、异界小岛、天使、星空、哈珀望远镜,无一不吻合,无一不在这本小册童书里再现。而小虫对它的喜爱尤不亚于我,霸占了一幅幅插图拷问我。
每来一本旧书,老王即问,要不要消个毒?我笑,书会有什么毒?难不成先泼酒精,后熏香片?倒是有点儿体会到董梁先生乐趣的我,恐怕终究中了旧书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