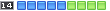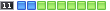一個特殊的合唱團
樹 立
這一天,在一個偏僻小鎮的一角空曠場地上,有一個特殊的合唱團在這裏演出。
這個合唱團總共只有三男兩女五個演員,他(她)們的年齡莫約在十幾到二十幾歲之間,雖然都是花季的青少年,但是他們和尋常人並不一樣,個個衣衫破舊,面容憔悴。人們再仔細望望,很快就看出來,這都是一些不幸的殘疾人:一位雙眼已經失明,三位不是缺腿就是斷臂,一位年齡最小的演員是坐在一輛破舊的輪椅上,她的雙腿動彈不了。
演員們在這片空地上架起一塊寫有《流浪合唱團》幾個大字的紅布橫幅,向人們表明他們的身份和從事的職業。演出的‘舞臺’中央,擺著一架外貌也像它那飽經滄桑的主人一樣瘡痍滿目的殘舊電子琴,這是這個合唱團唯一用來伴奏的道具。
前來觀看演出的只是當地的鄉衆和少數過往路人,從他們的衣著可以看出,這都是一些地道的平民百姓。幾十個人面對‘舞臺’,三三兩兩地分別站立著,圍成半個圈子,他們的眼晴都好奇地注視著面前這些遠道而來的演員和那台難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演唱道具,不過誰都沒有走開,而是懷著熱切的心情在等候演出。在這個偏僻的小鎮,是難得有什麽人會來這裏表演的。城裏任何一位稍有名氣的歌星,她們會到這個窮地方來嗎?身價不凡的 《同一首歌》更不用說了。
演唱會與高雅的音樂殿堂裏的演出不一樣,它樸實無華。場地上沒有鋪上名貴的地毯;沒有忽明忽暗的閃閃燈光;沒有令人眼花繚亂的伴歌豔舞;沒有請來衣著華麗、美貌出衆、口齒伶俐的節目主持人;觀衆中沒有事先約好的獻花者;台下沒有早就包裝好了的、穿著同一種服式、手裏拿著螢光棒助威呐喊的群體;更沒有出售象徵演員的高貴身份的高價門票 (連最廉價的也沒有)......但是,整個演唱會從頭到尾,演員們都是認認真真,全情投入,嬴得了觀衆的贊許。
演出的程序看來是經過仔細規劃好了的。最先,是演員中年紀稍大的一位用他那洪亮又好聽的男聲對著觀衆說:“謝謝各位,演出就開始了!”開場白只有這麽简單不過的一句話。
接著,就是那位下肢癱瘓的小姑娘用她的巧妙雙手,嫺熟地在電子琴上彈出一曲歡樂的《迎賓頌》,用它來揭開演唱會的帷幕。這輕快、悅耳、優美動聽的華爾茲曲調,很快地把聽衆都吸引住了。
不像其他的演唱會,它的最大特色是沒有報幕人多餘的說話。節目一個接著一個,安排得很緊湊。先是一位男演員獨唱《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這首人人喜愛的歌曲。在小姑娘電子琴的伴奏下,這首歌唱得十分之好:男高音的音色圓潤又渾厚,吐字清晰,深情無限地唱出他對‘美麗故鄉的眷戀’和爲了‘故鄉的景色更加美好’而獻身的誓願。感人的歌聲時而高亢,時而低沉。在這沒有任何遮攔的廣場,大自然環境中縱情唱出的每一個音符,都是未經任何修飾加工的。歌聲平地而起之後,隨著空氣的流動,飄上了古鎮的上空,它由強而弱,向著四面八方慢慢地散開去,但這已經變爲低弱的美妙旋律並沒有立即消失,而是餘音嫋嫋,在空中流連良久.....從而給人帶來一種無以名狀的難捨難分、悠悠神往的感覺。這樣的演唱效果,如果是在與自然隔絕的室內,那是絕對沒有的。得到了美的享受的聽衆,這時都不約而同地鼓起掌來,他們紛紛走向擺在合唱團面前的一個小缽子投入一些錢幣。
看到有人鼓掌和投放錢幣,演員們的臉上都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向觀衆頻頻點頭,他們沒有忘記向每一位投幣的人都說出“謝謝”這兩個字。如果投幣的是母親們攜帶在身旁的孩子,這時演員們更是彎下了身子,深情地望著那充滿稚氣的孩子的臉龐,用溫柔的聲音說:“謝謝小朋友!”
一曲由喬老爺(喬羽)填詞、谷建芬作曲的《思念》,由那位坐在輪椅上的小姑娘自彈自唱起來。演員的感情可謂真正是融進了歌詞的意境之中。用‘聲情並茂’這幾個字來評價她的演唱效果並不爲過。當她唱到‘難道你又要匆匆離去,又把聚會當成一次分手......’之時,歌聲如泣如訴,更是倍加婉轉動聽,聽衆既受到了親人別離時那種難以割捨的悲愴感染,也獲得了美的藝術享受。
演唱的全是人們喜愛的老歌好歌,久唱不衰的歌。接下來演出的有《草原之夜》、《鼓浪嶼之歌》、《敖包相會》和《外婆的澎湖灣》這幾首優美動聽、扣人心弦的歌曲。他們還唱出《三套車》、《北國之春》、《紅河谷》幾首有名的外國歌曲。一位男演員甚至獨唱《我的太陽》這首難度很大的義大利名曲。
當然,你不要苛刻地拿劉歡、毛阿敏、戴玉強或蔣大爲和這些人相比。《流浪合唱團》的每一個團員都確實唱得很棒!
隨著美妙的歌聲的彌漫、擴散和飄蕩,古鎮上聞聲而來觀看演唱的人更多了,會場的熱烈和歡樂的氣氛進一步在昇華。毋需演員們的自我作秀,說什麽“請大家給點掌聲好不好?”也用不著事先約好了的‘台下啦啦隊’的言不由衷的幫腔。自發的歡呼聲和掌聲一陣又一陣在人群中不斷地響起。放在演員前方的小缽子的錢幣也漸漸高凸起來了。
將近兩個小時的演出快到末尾了。他們恰到好處地、用一曲歡樂的《今夜無眠》合唱來結束這個集會。這時,會場的歡樂氣息更加濃郁,更加高漲。人們發現:隨著有節奏的美妙琴聲放聲歌唱的不只是那五位演員,還有許多忘情的觀衆,臺上臺下,他 (她) 們的感情都彙集在一起了。
就在人們即將離開會場的時刻,人群中走出一男一女兩個衣著樸素的中年人,他們的手中都各自拿著一張印有紅色圖案的100元紙幣,浮現著喜悅的面容走向投幣的地方。在這種屬於街頭賣唱的場合,竟然有人如此大方地用錢,這顯然是一個很不平常的舉動,因此立即引起許多觀衆的注意,人們對這兩個中年人紛紛投出詫異的眼光。演員們這時更是驚奇不已,忙著連聲道謝。一下子就有人給了200元,這容易嗎?這個放錢的缽子,經過了兩個小時的積累,雖然看來是已經盛滿了鈔票和硬幣,但這只是一些一元幾角的小額錢鈔,一總加起來也不過幾十塊錢,200元可是它的好幾倍啊!
這對中年人投幣完後並沒有離去,而是向殘疾人走去,主動地握著他們的手,動情地說:“你們說錯了,應該說謝謝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你們是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給大家帶來歡樂和美的享受!你們應該得到應得的報酬!只是我們的能力有限,這報酬太微薄了。”
殘疾人都驚愕了,他們是有生以來頭一回聽到這樣的說話,頭一回聽到這種有別於一般人的傳統觀念的見解,他們都噙著淚水,用疑惑的眼光望著大家,喃喃地說:“是應得的報酬?而不是做好事的對窮人的施捨嗎?”
中年人用堅決的語氣再一次更正,說;“不!是應得的報酬,而不是施捨!”
就在這個時候,人群中有人認出說話的這對中年男女,他們是受人尊敬的鎮上學校的老師,還是一對夫婦。立即,大家都圍上來了。
兩位老師看到有人想知道他們議論的話題,十分高興。男老師就繼續說:“說來都是舊的觀念的作怪,長久以來,人們總是把那些沒有經過包裝和渲染、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街頭演出當做下賤的賣唱,當做求乞;而享受了他們的演出的人這時如果給了點小錢,則自命爲做了好事善事,是對窮人的施捨。這是不對的!就拿今天這場演出來說,明明是一群不知名的街頭藝人通過他們辛勤的勞動,給我們帶來了精神上美的享受,但有些人卻認爲這些人是乞討者,是在向你乞求施捨?這合理嗎?究竟是誰‘欠’了誰?”說到這裏,男老師的情緒激動起來,臉都漲紅了。
女老師接著說:“當然,是我們‘欠’了他們的!他們也和我們許多人一樣,是自食其力的人,他們的勞動是應該得到尊重、得到報酬的!特別可貴和可敬的是,他們還是不幸的殘疾人。他們現在有這樣良好的音樂修養和表演能力,並不是天生的,而是經過刻苦磨練的結果,如果沒有堅毅的意志,他們是做不到這點的。我是一個音樂教師,我看得很情楚。”
人群中一位上了年紀的人也說話了:“兩位老師都說對了。這些殘疾兄弟都是憑著他們的勞動自食其力的人,應該受到人們的尊敬。殘疾人的痛苦,需要世人的是同情,而不是憐憫。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有做人的莊嚴!”
另一個青年人接著說:“我們應該擺脫世俗的偏見,不能再受舊的觀念束縛了。試問:這些殘疾兄弟有這麽好的音樂素質,如果是在城市裏,經過人們的‘包裝’和商業的‘炒作’,在大衆的心目中,他們還是街頭乞討的賣唱者嗎?”
..............................
演唱會是結束了,但‘演出’還在繼續著,而緊接著‘上臺’的,是一場人們事先想不到的、很有意義的、向頑固的世俗偏見吹起‘討伐’的號角的特殊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