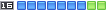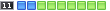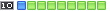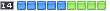|
|

|
||
读书会(二)
[ 这个贴子最后由冰云在2017-6-16 13:21:24编辑过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萧总版主读得用心,剖析深入,作为作者,最感欣慰的就是作品被有眼光者欣赏了。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在诗词里长醉 在生活里长醒
|

|
||
[ 这个贴子最后由树立在2017-5-25 18:16:31编辑过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

|
||
| ||
美华文学论坛感谢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