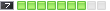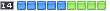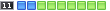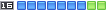三
1972年底,主持湖南省工作的军队代表卜占亚因故调离,已调中央的华国锋回湘,单独召见了胡勇(汽车电器厂)、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等人,“工联”派扬眉吐气了,主要领导人胡勇当任了省革委副主任,唐忠富两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出任省总工会主席,“工联”派的雷志忠(省汽车运输公司)担任了长沙市委副书记。“工联”的基层头头相应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
“工联”派“海燕”的赵家林,进入长沙港务局三结合领导班子,担任局党委副书记,赖宇明出任局团委书记,还有“海燕”的叶其康、刘延春、谭可成等人都在局下属各级革委会中任职。
1973年9月,省航运局调整各港运载力,我所在的铁甲板驳移交常德港,交船后我从常德乘长途客车回到长沙,从革委会成立之日起,长沙港实行政治建港、军事建制,全港的客轮、轮驳大队,三个码头作业区以及其他车队、工厂下属基层班组、车间均称之为连、排,我所在的225队甲板驳原归属轮驳大队第四连,回来后,大队人事调度员让我仍回四连报到。
随即我向轮驳大队领导提出请求,为照顾多病瘫痪的母亲,要求调到回长沙机会多的拖轮工作,大队人事调度室主任王清福同意了,却遭到驳船四连连长陈楚平的反对,他先以连队缺员为借口,王主任同意在新招青工中多分配二个人补我的缺,陈楚平又提出技术骨干被调走会影响整个连队的生产,坚决反对调我去拖轮。我思前想后,始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气得易双桂提着根木棍要到水陆洲连部去教训他。1984年,我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托我的朋友李星罗来说项,也没说出1973年阻止我调动的真正原因。1987年他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专程从丁字湾到长沙请我去他家,席间说了许多真诚感激的话。
长沙港务局的传统习惯于把船舶分成三等:客轮、拖轮和驳船。客轮航班定时定点,工作生活有规律,是船员最理想工作的环境;拖轮机动性强,在长沙待拖船员的机动时间多于驳船船员,况且每月中必定在长沙检修四至五天;驳船进港后要忙于装卸货物,即使是待装待卸时,也不能随便离船,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开始作业,只能在待航时,到船舶调度室问清出航时间才能匆匆回家一趟,驳船一出航就莫问归期,在外港的待航、待装卸、以及货源的流向,下一个航班去哪里,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离长沙三、五个月是常有的事,还要经常停靠在荒无人烟的河汊小点、滩头洲尾。
鉴于不能调到拖轮,我平生第一次拒绝接受船舶大队回四连报到的调令,僵持了四十五天,不上船也不去领工资,第二个月,终因家中经济拮据,我便想退而求其次,上四连驳船中条件最好、最稳定的航线船“快速班船”,这个要求大队领导同意并直接下了调令。于是,我到人事调度室要求补领工资,调度员拒绝审核,并向副大队长程甲东汇报,程甲东听完汇报,严厉地说:“矿工四十五天,完全可以除名了,工资必须扣发,再不上船就作开除处理。”我又是平生第一次同顶头上司程甲东大吵大闹起来,他觉得有伤颜面,匆忙离开调度室,我追上二楼,在他办公室里拍桌打椅,吵闹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的党总支书记(教导员)言金鉴,他把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争吵的原因,我气愤地说出要求调动和上快速班的理由,言金鉴听完后,立刻打电话给陈楚平,令他安排我上快速班。又让程甲东交待人事调度室,让我补领了上月工资,第二天我在西湖桥码头(现在的杜甫江阁)上了151队3号木驳船。
快速班(线)是一条拖轮边顶一条木驳,定期定点运送鲜、活农副产品。长沙港有两条这样的固定航线:一、长沙至常德,四天一个来回,长沙、常德装卸两天;二、长沙至茅草街,六天一个航班,在长沙装卸两天。快速航线是承运湖南省外贸在茅草街和草尾收购的鸡、鸭、柴鱼、鳖、黄鳝、蛋等鲜活物,从长沙转运出口。回程运送政府调配给茅草街、草尾一带的日用百货和烟酒糖等物资,在这条航线工作的船员常能买到极其廉价的农副产品,每个航班还能在鸡笼鸭笼里捡几斤蛋吃,所以全大队的船员都说“是个肥缺”。死鸡鸭0.2元一只,死洋鸭和洋鸡0.4一只,死柴鱼0.2一斤,船员买到的宰杀晕头的鸡鸭。
我在湘西的那段日子里,调到市总工会当通讯员的易双桂,经常一人到河西,陪我母亲聊天以解她思子之苦,又常邀在装卸机械厂上班的罗国华结伴看望我母亲,还常常放下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其实他俩的家境也不好,双桂有多病的母亲要养,国华下面三个弟妹没有工作。母亲在晚年无数次提起他俩,满足地回忆起与他们的交谈,话语中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1974年下半年,已经调到长沙水泵厂的易双桂,站在西湖桥码头等我,我的船刚停靠好,他上船就抱怨说:“他们好过,当官了就不管弟兄们。你应该去找他们,要他们调你上岸。”我知道双桂是要我去找赵家林他们,但此时的我,早已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命运,而且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很肤浅,需要不断提升,水上是最好读书和修身养性的地方,再者,性格也决定我不会开口求人,特别是为自己求人,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当我觉得水上对学习没有帮助之时,就是我离开之日!我让他等着,我俩终有欢聚在陆地上的一天。
从三线参运回来后,虽然仍航行在湖南内河,因为航班定点定时,我与在长沙港装卸机械厂当钳工的刘利国,见面交谈的时间多了很多,他是我参加航运工作后最好的朋友,一起休假,一起学雷锋,一起参加文革,他家住石门坎夏有里,我没少在他家吃住。自1972年后,他父母的势利和利国的实用主义行为让我渐生反感,在对理想和现实的认识上各持己见,对生存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处置上渐渐大相径庭,我厌恶趋炎附势,而他母亲一见到赵家林、赖宇明升了官便立马攀亲认干儿子……渐渐我和利国常因话不投机而不欢而散,最后一次长谈时他恳切地劝要我面对现实,少点书生气。他现身说法,大谈处世圆通的好处,大谈金钱权力的作用,大谈学以致用的要诀……我越听越烦,因为我脑海里已镌刻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知足常乐”、“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古训,哪里还听得进他的话?我的轻蔑态度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终于愤愤不平地站起来说:“我的哲理,是二十多年的生活积累,事实也证明了我过得比你好,要不是朋友,我才不会讲得喉干舌燥。好心没好报,再不同你讲这些了。”此后我和他最早建立起来的友谊归于了平淡,见面只剩“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寒暄了。1984年我获升迁后,他又像最初时一样亲密地邀我去他家,伯父伯母也平添了七分殷勤,双双为我夹菜,利国说:“你是我们六二年同事的骄傲。”刘伯父说:“我早知道你不是平凡之人。”刘伯母反复叮嘱“常来噢!”1985年,刘利国在其娘舅帮助下移居美国后,我还是尽心尽力为他办好几件事(购房工龄和上海到长沙货物托运)。
1974年2月,船上政工员向我们传达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易双贵、罗国华、刘利国等在岸上工作的朋友,都劝我再找赵家林,调上岸参加运动,因为他们常听我讲述“孔孟”和“四书”以及中国历史,知道我已不同于从前了。
三十而立,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再属于我,我再不会盲目投身蒙自己于鼓中的任何政治运动了。我用已获得的知识理智地看待、分析这场政治运动,不想借用时势来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我认真地阅读上级发到船上的所有法家著作,细读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同时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书,经过近四年的自学,我信奉孔子的学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在长沙港务局大批判组里同那些笔杆子们辩论时,也骄傲地宣称“我是拥孔派”,因为我知道,对待一个最底层的工人,是不会拖出来批判的,否则的话,我是不会充当出头鸟的。
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孔学的被帝王利用,应该归罪于统治者和御用文人,是他们曲解篡改孔子的思想和言论。正如出了马列主义,应运而生修正主义,难道要归罪于马克思和列宁吗?”
1974年3月,我的船一进港,匆匆过河回家看望母亲和二岁多的外甥刘彦,姐夫在客轮当大副,姐姐在客运站物资供应处,两人工作很忙,母亲承担起照料外孙刘彦的任务,因此我每次回港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探视。
这次回家,正逢刘彦的后背脊梁正中长了个疮,红肿疼痛,整日哭闹,邻居张二嗲用草药敷治了几次不见效果,听人说这是背花,相当严重。我忧心忡忡地回船,在客运码头上巧遇罗中光,忧伤地向他诉说了刘彦的病情。罗中光醉心武学,我、王伯纯和他三人曾一同向李世强学习武术,只有罗中光坚持了下来,现在他又开始学习用中草药治疗跌打损伤,他安慰我说:“放心,就一个包,我去看看,没问题的。”罗中光在客轮上任水手,二天回一次长沙。
本来是六天一个的航班,不料船到茅草街卸载后,临时抽调到常德,半个月后我才回长沙,心急火燎地赶到荫马塘,刘彦欢呼雀跃地跑出来迎接,他已经痊愈了。母亲说,你的朋友罗中光真好,你走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来了,看了看红肿的疮,出去采了些草药,在嘴里嚼碎给刘彦敷上,刘彦晚上就睡了个好觉,临走时告诉母亲别动膏药,待他后天来换。第三天刘彦早早站在大樟树下,望着马路不停地问:“罗舅舅什么时候来?”罗中光准时准刻,利用在长沙的时间,从中山路轮船客运码头跑到河西天马山荫马塘为刘彦换药,九天就痊愈了。我揭开刘彦的衣服,他脊背正中只留下一粒绿豆大的疤痕。
后来,罗中光告诉我,这种疮的确叫背花,只要懂得治,它就是个小疖子,不懂得治会要人命的。他还告诉我,今后凡长了无名包疖,你先用柳树尖、楋树尖,还有一味药我不记得了,把三位药等量采齐,在口中咀嚼成糊状,敷在包疖上,可以遏制包疖的生长,然后从容找能人医治或是送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