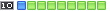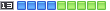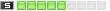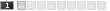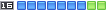我对荷,内心仰望已久。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上有茂盛的扶苏,池里有美艳的荷花。)荷,从《诗经•郑风》里走来,一出场,就风姿绰约; “青荷盖绿水,芙蓉发红鲜。”“清风徐来绿云涌,闻于疏处窥渔人” “从来不著水,清净本因心” 等诗句,使荷在百花园中更是极尽鲜妍。
同学偶然的一场小聚,成就了这场迟来的花事。
路两边全植着速生杨,看样子年份不多,茎干纤细,碎碎的叶片在风中闪闪烁烁。绿茵茵的秧苗,正抽穗的稻子,把田畴点缀的或绿或黄。田间地头,间种了棉花和芝麻,棉花开着白的、黄的花,有的已结出棉桃;芝麻顶端开着细小的白花,绿色的籽儿一对一对挨着往上长。在坑坑洼洼的小路颠簸了两三里路后,我们眼前终于出现了同学家的老房子,那片田田的荷塘随之映入眼帘。迎接我们的是同学的伯伯和奶奶。他的伯伯皮肤黝黑,饱经风霜的样儿,奶奶是个瘦小精干的老妇人。
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打在挨挨挤挤的荷塘里,好似演奏一曲急行军曲。我只好摘了一片荷叶,权做雨帽。站在雨中,看着雨滴跳珠儿似的在荷叶上滚落,清芬淡雅的荷香沁入肺腑。“水面清圆风举荷”,初秋的风儿,促狭地轻掠红蕖,雨滴儿贪婪的亲吻花瓣儿的红唇。荷塘边泊着一艘孤独的船,酷似我们儿时折过的纸船,尖楞,小巧。他伯伯说,那是采莲船。
“能坐么?”
“当然。”
“你不能去。”
“为啥?”
“多坐一个人,船在荷塘就活动不开了。“
我眼巴巴看着他顶着一顶荷叶帽,轻摇小舟消失在藕塘深处。
早已错过了蜂围蝶绕的盛夏,昔日立在尖尖角的蜻蜓开始做初秋的梦了。我的目光穿梭在水面和花朵间,揣不出荷塘深处的禅意,只好任迟来的愧悔,在眉间心上徘徊。
一朵朵微含水意的荷花,摇着叶影,驿动着一池微凉的水波。相传,荷是爱情的守候,冰肌玉清的玉姬,将无尽的忧伤,包藏在流泪的花蕊中。半开半合的,欲语还羞,使人想起“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诗句;怒放的秋荷,花瓣繁复,蓬儿杏黄、穗儿纷披,钩针样儿的花柱,娇艳动人。但不管是啥样的荷花,皆从密密的荷叶间挤出,如剑如戟,亭亭玉立。荷叶,大都有些残败,深绿的表面霸道地被一小片的土褐侵占,且有不断扩张之势,“红藕香残玉簟秋”,再过一段时间,将只能“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然而此刻,我情愿赋予它轻松的基调,想像自己是两千多年前一个采莲的女子,皓腕明眸,窄袖轻罗,低头弄莲,箫声隐隐: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彼泽之陂,有蒲与莲。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
……
可惜,我的幻梦难续,他伯伯载满莲蓬归来了。几枝箭似的荷花插在莲蓬中间。船靠岸后,他伯伯就走开了。我蹲下,折断莲蓬连着的茎干。他奶奶拿来了一个塑料袋,我稍作清理就把莲蓬往袋里装。莲子中间乳头状的突起时不时划着了手,针刺般的疼。他奶奶伸出手说:“你看,这都是以前摘莲蓬时划伤的。”她的手臂、手掌上红褐色的划伤累累,以前我只知道采莲是多么风花雪月的事,没想到期间也有如许辛劳!看来文学的浪漫与现实的冷酷之间,距离不可小觑!
雨,不知啥时停了。秋荷满目,我想,她们本该在盛夏开花结子,却在相思苦旅中一再坚守延误至今。心成熟了,也就成熟了痛苦。我默念她们曾经的韶光,遐思月夜清露的滴响,想那细细密密的藕丝如何牵系遥远的相思。我知道,我只能带走一个花事阑珊的记忆,却无法参透一粒籽儿缔造出的煌煌生命。
秋荷们相依相偎,执着地捍卫作为莲的名望与尊严,从这点来讲,莲,比某些人高尚。
深深的,我为秋荷俯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