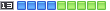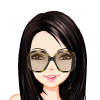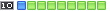电话中母亲说,今年夏天北京特别热,前一阵到摄氏四十度以上。跟悉尼不同,北京的夏天,不知为什么,三十摄氏度以上,就很难受了。四十度以上,还不得烤箱蒸笼一般。在凉爽的南半球,想象着那种难受。唉,环球不同凉热。
北京的夏天很漫长,很难受,可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北京的春季特别短,当年每到“五一”节,总是有庆祝游行。一系列的富有新中国色彩的节日也相继而来。“六一”是国际儿童节,“七一”是建党节,“八一”是建军节,到“十一”是国庆节。生命之树,留下的一个个稚嫩的年轮,透出褪掉的红色。
五月来了,毛衣就可以脱了,轻松地穿着单衣在阳光里走,抬头看天,阳光总是刺得睁不开眼睛。头上,后背上被烤得热热的,感到刺痒。又要出痱子了。那些又痛又痒的小包包,每到夏天就来光顾我。六月的时候,可以穿裙子了。女孩子们害羞,都想穿裙子,又轻易不敢穿,就耐着性子等着。一旦有一个穿了裙子出来,马上个个都换上裙子,走到一起,比较裙子的花色,长短,宽窄。还要原地转上几圈,让裙子开出一朵朵喇叭花来。穿裙子,须配凉鞋。凉鞋是个极好的发明,塑料做的,便宜实惠,宽大舒适,四面透风,不需穿袜子。下雨天,不怕被打湿了,脚脏了,连鞋带脚在水管子下面一冲。
人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其实,困,乏还有打盹,都该是属于夏天。午休时间加长了。在蒸腾着的热气中,一切都昏昏欲睡,只有开成小喇叭形状艳丽的草茉莉发出一股让人熏醉的香气,树上的知了也不停地“知——,知——”地叫。人们兀自在家中小憩一个钟点左右,又睡眼惺忪地上班上学去。洋灰的地面,已经被太阳晒得火烫,路上的沥青,都是软软的,鞋底上的图案,自行车的车胎印,都清晰地印在上面。
许多新鲜菜蔬开始上市了。一车车的西红柿被拉进城来,堆得小山一般地高。记得有一年大丰收,果实又大又红,一毛钱能买上好几斤。西红柿既是菜又是水果,可以生吃。我喜欢糖拌的,还有西红柿炒鸡蛋。我还喜欢吃豆角,茄子,蒜苗。有一种又大又圆的茄子,特别鲜嫩好吃。不像澳洲的茄子,皮厚,肉干,味道也发苦。青椒、黄瓜、芹菜、韭菜、莴笋也是夏日的时鲜菜。我是从小脖子上挂钥匙长大的孩子,(父母都上班,家里没有大人的孩子脖子上通常挂把门钥匙。)很小就学会的买菜做饭。记得学会炒的第一道菜就是土豆炒青椒。谁家做这道菜,孩子们就唱起一首儿歌:“嗦嗦嗦咪嗦土豆炒辣椒,你爸爸爱吃你妈不给炒。你爸一生气,你妈一叉腰,两口子打架真呀真热闹。“
夏天还有不少水果,有桃、李、杏、葡萄、香瓜等等。水果是奢侈品,人们不是经常吃。但西瓜上市的时候,是成卡车地从外地运来,又多又便宜。大人们喜欢下班以后买上一个托回家。放上半桶北京特有的清凉的自来水,把西瓜冰上。吃过晚饭后,院中树下,坐在小板凳乘凉,当白日的暑气悄悄地退到夜幕之后的时候,把西瓜切开,瓜香飘散在夜风中,家人们一起享受这甜美多汁的夏日水果。
天热时,妈妈喜欢念叨:还没有数伏,天就这么闷热了。到真的数伏的时候,又叨念着;现在是头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她有气管炎,怕热天,特别是气压低时,她喘气困难。天气闷热食欲不振,她喜欢做凉面。把煮熟的面条,用水冲凉,拌上黄瓜或者煮熟的豇豆,再加上香油、蒜泥等调料。吃起来清凉可口。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北京的三伏天,热得人浑身都是汗,黏在身上不干。妈妈在床上铺上凉席,晚上用凉水擦洗一遍,睡在上面就凉快许多。有时晚上睡不着觉,端一把小凳,坐在院子扇着扇子乘凉。外面街头,路灯下也有不少乘凉的人们。还有不知从哪儿飞来成群的硬壳虫。我以为是萤火虫,一个个地抓来,放在玻璃瓶子里,等着它们发光。它们或许是由于气候原因飞来的。
夏天的气候,很难捉摸。“六月天,婴儿脸。”人们是这样说的。闷热的时候,妈妈就说:这是憋着一场雨呢。果然,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变阴,电闪雷鸣地下起暴雨。但时间不久就停了。有一年北京的雨下得特别大。院里的积水深到小腿,雨停后,我们一群孩子兴高采烈地出门趟浑浊的泥水玩。孩子爱水是天性。每到暑假,后海游泳场开放。我们几个总是结伴去游泳。不干净的水,里面密密麻麻泡得都是人。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橡皮救生圈,我从小就套在身上游,结果因为它,很多年都没有学会游泳,直到后来长大,救生圈套不进去了。才学会自己浮起来。
听到罗大佑的歌《童年》,总让我回想起北京的夏天,我的童年,就如漫长的。昏昏欲睡的夏天,盼望着游泳,盼望放假,盼望着长大。可不觉之中,很多个夏天就过去了。光阴飞逝而去,我不再盼望了,因为岁月只有让人变老。但还是喜欢夏天。也怀念北京的夏天。
记忆中故乡的夏天,久违了,也永远地别了。因为夏天还在,北京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北京了。
2009-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