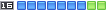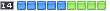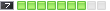第一次绝望
为了减轻母亲肩上的压力,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便在假期和星期天里去推板车挣钱。1958年暑假,天气异常炎热,我匆匆吃完早饭,举步朝门外走去,被十一岁的大弟弟宗元叫住,他说今天定要一起去推板车,宗元从小多病,自被蛇咬后,身体更是虚弱,家里的重活从不要他做,自然不会让他去做推板车这样重体力活;可我禁不住他的死缠烂打,只好带上了他。
看着有两个人,我就到阜埠河码头去找活,同一个推上岭推熟了的拉板车工人谈好价钱,我和宗元同推一辆车,从阜埠河码头到中南矿冶学院(现在的中南工大)最南端的建筑工地,每次一车装运一千多斤红砖,单边路程十二里,一趟工钱0.6元。那天太阳特别辣,我和宗元汗流浃背,第一趟完工已是十点多,为赶时间,工人用空板车拖我俩回码头,第二趟完工已到下午二点了,我接过一元二角钱,拉着弟弟高高兴兴回家,宗元早就在叫饿,我也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便在矿冶学院大门口的大饼摊子上买了一角钱大饼,两人分食,狼吞虎咽几口下肚,什么味道也没吃出来。晚上把剩余的1.1元交给母亲。
晚上我早早地睡了,半夜里听到母亲焦急的声音,睁眼一瞧,母亲正在问宗元“哪里不舒服”,姐姐站在一旁,递送着冷毛巾。我问妈妈宗元怎么了,妈妈说宗元发高烧,浑身滚烫,右肩与颈交接的地方长出个大疖子,通红通红。天没亮母亲急匆匆地搀扶着宗元去了长沙市四医院。
整整一星期才治好他的疖子,打针、吃药医药费用了近四元多,我俩推板车交给妈妈的钱才1.1元,治病花去了它的三倍多,真是得不偿失。
从此,我再也不敢带宗元去做这样的重体力活了。
自人民公社化后,灭绝了个体小商小贩,我家那个巴掌大的的小摊也关张了,全家生计只剩下母亲替人织毛衣一条路。
1955年8月,国务院相继公布实施《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实行四证三票制: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
最初的粮食定量还宽松,母亲口粮按劳动者定量,为31斤,取消小商小贩后减至27斤,再减至24斤;姐姐读中学定量30斤;我和宗元26斤和24斤,宗平18斤,每月定量的粮食尚有结余。
1959年初苦日子来了,物资匮乏,一切生活物品定量供应,食油定量减至每人每月2两,我家一个月食油仅有1斤。接着各种票证相继出炉,全国国票、地方票多达万种之上。猪肉供应逐年减少,直减到每人每月2两,肉店每天挂出瘦不拉叽的几十斤肉,不到一小时就售完了;禽蛋类和牛羊肉等干脆从人民的视线里消失了。最苦的时候,蔬菜也发证供应,每人每天半斤,蔬菜定量还不见得能全买回来,国营蔬菜店的菜顶多能卖两个小时,店门一开,人群沸腾争先恐后,抢不到菜的人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货架兴叹,因为蔬菜的定量隔天就作废了。中央号召“低指标、瓜菜代”, 一切土地归公社,田都种不好,哪来的瓜菜?
鱼(按节日配给)、肉、豆腐、食盐、火柴、肥皂、布、棉花、糕点、香烟、糖、煤、煤油等一应生活物资全部按人口户头发票供应。百货商店宝笼柜和货架上摆放的只有瓷碗、搪瓷类货物以及日记本、钢笔文具类货物,偶尔看见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几只手表,那是为体现物资丰富社会繁荣、为点缀国营商店而陈设的,因为购买它们要凭特供票,一般这些物品是在特供商店里购买。
全国人民生活艰苦已达极限,我家更甚,从1955年10月到1962年10月整整七年里,我们姐弟难得吃一根三分钱的冰棒;即使在外劳作得喉咙眼里冒出火来,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喝一杯大碗茶。
口粮定量每月母亲减至22斤,最小的弟弟18斤,宗元24斤,我和姐姐27斤。用在物资丰盛的年代,这个定量真的多了,谁也吃不完,要知道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吃,就是用于喂猪的细糠都成了营养品,只有患上水肿病的人才有少量配给。山上、田边和路旁的各种野菜、蒿子、槐花全采光了,那几年走在大街上,满眼全是面色蜡黄、骨瘦如柴的人,看不到一个孕妇。
经历了那个岁月的中国人,想起三年苦日子都会心惊肉跳。
我们的口粮本来就不够吃,又缺盐少油,蔬菜时有时无,没菜时最好吃的就是用酱油拌饭吃。每餐吃不饱,母亲还不得不减少我们每天的定量,抽出一点粮票卖掉,用这点钱买回其他的配购物资。我和弟弟们经常坚持把一天的饭一餐吃,但求饱餐一顿过过瘾。
1960年6月,姑妈突然带着二弟宗亮从合肥来到长沙,姑妈说:“宗亮不听话,学习不认真;总在河边玩,万一出了事,嫂嫂带的儿女个个听话,我怎么交代呀!所以送了回来,一则让嫂嫂教育他,二则你们一家该团聚了。”姑母承诺今后每月寄给我家的生活费从10元增加到20元钱,她会竭尽所能帮助嫂嫂养大五个孩子。要是没有舅舅和姑母,光凭母亲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支撑下来的,我们弟兄肯定逃不出骨肉分离的厄运!因为舅舅、姑母寄来的钱,可以买回定量的大米,大米时价每斤0.098元,至少可以靠买回来的大米维系生命。
初见二弟宗亮,他的确比我们好动得多、调皮得多,常喜欢在小弟宗平身上练手掌劲,宗平挨了打从不告状,有次我看见他手掌在宗平身上砰砰地打,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一点就透,从此学着我们的规矩,兄弟间友爱和睦。
1959年10月中旬,学校组织的支农活动,到长沙县谷山公社秋收,农民的生活很艰难,公社集中为学生开火做饭,我们按定量上交粮票,为让我们能多吃点,公社在每餐的饭里掺杂些红薯,大锅大灶,还是柴火饭,特别的香。每天下午,公社还派人给在地里干活的学生发一个生红薯。没有菜,几乎顿顿吃从地里挖出来的蕹菜根,无油少盐煮得稀烂,我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十五天后回校,我把省下来的十几个红薯带回家,全家人饱餐了一顿。
从1955年9月到1960年10月,母亲拖着条跛脚,克服着心痛病,忍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劳累着,她的心病和腿病就越来越重,特别是腿,经常痛得寸步难移,歇歇停停依旧奔走在荣左路上。每次脚痛得无法忍受时,她就在棉花厂药店花0.06元钱买二包“何济公”粉剂,和着唾液吞服下去,重新上路。母亲能喝点酒,一两“冯了性”药酒能止住她的痛,而且比“何济公”粉剂效果强好多,为了省钱,妈妈总用“何济公”粉剂镇痛。经常看母亲买药的售货员于心不忍,关切地劝妈妈少吃“何济公”,喝点“冯了性”药酒对身体好些。母亲摇摇头笑笑说:“不行啊,五个孩子要吃饭啊!”
1962年9月,我和姐姐参加了工作,我间常给她买瓶药酒,“何济公”的用量减少了,直到1964年才与“何济公”绝缘。1966年仲夏,我从外地回到长沙,利用船在港口的时间回家探望母亲和弟弟宗平,宗平欢笑着跑到我身边,问:“带回什么好吃的东西?”一见我从书包里拿出瓶“冯了性”,他的欢乐顿时消失了,哭丧着脸说:“哥哥,莫再买药酒了,叫妈妈也莫再喝酒了。”我忙问出了什么事,宗平说:“前几天妈妈喝了药酒,突然大哭大笑,怎么也制止不,我以为妈妈疯了,吓得半死。”看着一脸愧疚的母亲,没等我开口,母亲说:“我保证今后再不喝酒了,宗凡,你在水上工作,风湿重,这些药酒你拿去喝。”我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触动了她心底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一时不能自已,哭一场将胸中的郁闷吐出来,未必不是好事。我和姐姐每月工资34元,各寄回家20元,40元维系分开的两个家,着实难得很,1962年9月父亲带着二弟宗亮回到零陵乡下,母亲和二个弟弟住长沙。母亲心里的苦和难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想到这,我笑笑说:“没事,还是喝点吧,控制点量就行。”母亲的脸又呈现昔日的坚毅,决绝地说:“不喝了,你买伤湿止痛膏吧,以后只用膏药。”
1960年6月,我家从麓山南路12号迁居天马山下荫马塘7号,这原是邓姓两兄弟的一个大院,邓家老大在土改定成份时被划成地主,他的大部分房子被政府没收,只留给他们一间半做住房,没收的房子归岳麓区房管局,房管局分配院子西北角的一间正房、一间三角形的小厨房给我家居住。
院子南墙外长着一棵大樟树,树龄已过百年,树干要四个大人手牵手才能围住,大树笼罩着大半个院子,树冠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如华盖一般,苍劲的躯干爬满岁月的皱纹,镌刻着风尘的痕迹。大树张臂迎风,伸手留云,月上枝梢,满院银光点点,显得格外清幽。树冠浓密处有二个鸟巢,为数不多的鸟,飞翔和鸣唱都恰到好处,不惹人心烦而给人以身处大自然的愉悦。夏天骄阳似火,小院里树影婆娑,十分凉爽,是小院人家钟爱的纳凉地。
院子西边一条三米宽的小溪流过,四季常流不息,溪水来自岳麓山流向荫马塘,溪水最浅时有一尺深,常见游鱼戏水;每逢春季,溪水满沟渠深约一米多,荫马塘的鱼窜入渠沟,逆水而上,站在溪边,用漏网就可捕到一、二斤重的鲤鱼。
院里住着六户人家,湖大司机邓炳炎一家,原房东邓照明一家,卖甜酒为生的柳妈妈一家,湖大理发师胡妈妈一家,张建母子一家和新搬来的我们家;六户人家子女加起来有十四个,孩子和孩子是自来熟,按年龄我就成了娃娃头,都管我叫 “大哥哥”,现在最小的孩子也过了五十岁。
1960年9月,母亲瘫痪了,过度劳累加上长久的营养不良,母亲的风湿病再度复发,手脚关节一夜间全部变形,整日躺在床上,痛得日夜呻吟,到晚上又怕吵醒我们,咬着嘴唇强忍,早上起来,总看见母亲带血的嘴唇。祸不单行,母亲又患上水肿病,全身浮肿;肺也出了问题,干咳不已。经群众评定,居委会送来几样营养品:二斤细糠、半斤黄豆、一瓶橘子罐头。
街坊四邻都说母亲难逃此劫,这让我忐忑的心更加惊恐,母亲却轻描淡写地安慰我们说:“我是盆箍,盆箍断、盆就散架了,家就像一个木盆,我一死家就散,放心!我肯定不会死,一定会看到你们个个成家成才。你们也不要绝望,要相信‘粪堆也有发热之时’。”母亲凭着这个信念,无畏地直面疾病和死亡,说起来真的难以置信,母亲在没看过一次病、没吃过任何药物的情形下,活了下来,还活到了二十一世纪,是荫马塘他们那代人中唯一活到新世纪的老人。
母亲累到了、病倒了,为了活下去,我和姐姐不得不辍学四处找事做,努力寻求稳定的工作,没有地方招收十五岁多的孩子,我只得打些短工和零工。
街道居委会介绍我去了几个单位,都是因为出身的缘故不予录用。我随同学的哥哥到河东的建筑工地,想报名挑土方,那个工头乜斜着眼左瞅瞅、右瞅瞅,轻蔑地说:“不要!太小了,只会喝别人的血。”工地挖土运土按立方计算工钱,工头手下一般有二三十个人,轮流挖土和挑土,工钱是平均发放,人小不能同壮劳力做出一样的劳动量,同等的分钱无疑是侵占了他人的利益。
四处碰壁,居委会借给我一部破木轮板车,它不同于使用内外胎充气的胶轮车,木做的轮子,一条二寸宽的橡皮带包垫着轮子边,以减少与地面的摩擦力,可以稍微减轻拉车人的劳动强度。这辆木轮车的左轮橡皮带中缺了二寸,轮子每在地上转一圈,就重重的咯噔一下,车子的重量在肩头上颠压一下,去修理又舍不得钱,那时候小呀,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去找一块同样厚薄的橡皮,把它钉在缺口处,就不会遭受板车无休止颠压的折磨了。
有了这部板车,我每天到湖南大学家属区,家家寻问要不要买煤送煤,谁家需要,就把煤证、钱和盛煤的家什交给我,我到八字墙的煤店买煤装框,再把煤送进他们厨房指定的地方,一百斤煤收0.3元的工钱,一次能运送三至五家的生活用煤。湖大建设村在岳麓山南的坡上,煤最难送,而且也不加钱,板车拖不上去,只能把煤车放在坡下马路边,然后一担担跳上去,坡有一里多远,每挑一担煤上去要歇好几次,车子在路边等候时还要一个人在马路边守着,大部分时间是姐姐协助我卖煤送煤守车,她不能协助时,我将煤车拖到建设村坡下,在马路上大叫弟弟来,建设村坡下距荫马塘7号大约一百多米远。
就是这样送煤的事也不是天天有做,一天能收到三四家的煤证就大幸特幸了,因为能挣一元多钱,经常为收不到煤证而发愁。没有煤运送的时候,我拖着板车带着撮箕扫帚到阜埠河码头和路面上收集散落的煤,运气好一次能扫个十来斤煤,积少成多,积到几十斤就卖掉,也能挣上几块钱。
有次运煤,天下大雨,我和姐姐把油布盖在煤箩筐上,自己冒雨,浑身湿透了。姐姐当晚病倒了,姐姐在附中上学时,特别积极,处处争先,在京广复线的劳动竞赛中,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劳动过度,突然休克,老师和同学把她送回家,饭都吃不饱,哪来钱看病?营养更谈不上,身体怎么能够恢复?她的头痛头晕日益加重,以致只能长时间卧床休养,休养中,她向居委会借了部纺车,接乱麻纺线,纺成麻线滚成团交居委会,麻线是按斤付工钱的,为多挣钱姐姐总是纺麻到深夜,价钱太低,劳累一个月也挣不上10元钱。
1961年1月下旬,舅舅和姑母知道我在长沙难找工作,就寄来二十元钱,要我到合肥去碰碰运气,正巧小表哥所在的汽车队招砸焦煤的临时工,我可以先做临时工再寻求招工的机会。我归还了木轮板车,在街道办事处开了个探亲的证明,兴冲冲地独自奔赴合肥,十五岁的我,一路上做着许多美丽的梦。
从武汉到芜湖六百公里水路,沿途停靠,客轮顺水航行要二十四个小时,我买到最低5.8元的统仓票,统仓在船最底层,座位少,人多,船上百分之七十的旅客都是席地而坐。上船后我找了个角落栖身,听着机器的轰鸣声,带着对前途的信心,天刚黑我入睡了,这是大半年来第一个安稳的觉。五点醒来,我的周围东倒西歪靠着许多旅客,旁边坐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单薄清廋,在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见我醒来,关切地问:“小弟弟,你一个人吗?”听到同母亲一样口音的南京话,我倍感亲切,点头“嗯”了声,他收起书与我聊起天来,他说自己中专毕业,在马鞍山钢铁厂当技术员,到九江出差,现在是回厂去。我毫不保留地告诉他:家贫,初中肄业,独自到合肥投亲。他叹息了一声,说:“还是要多读点书啊。”随后聊些我能懂的三国水浒的故事,见我用白开水吞咽母亲为我烧烤的两个细糠面饼,他默默地站起身,拿过我的搪瓷杯,回来递给我一杯滚烫的水,说:“糖开水,你喝吧。”几年不知糖滋味,我竟一时手足无措了,一户人家一个月几两糖,这么金贵的东西,谁舍得给人,他还泡了一满杯,尝尝真甜,我感激地看着他,他却同我讲起武松来。到芜湖前,他拿出一张纸,边说边写:“我叫马安植,地址写在纸上了,以后给我写信吧。”又带着遗憾地说:“你记心这么好,三国水浒比我还熟,不读书真的可惜了。”
下午船到芜湖,我依依不舍地告别马大哥下船去轮渡码头,过河到裕溪口,坐火车到合肥,一路上在庆幸自己运气好、兆头好。
芜湖过河到裕溪口,二个多小时火车到合肥,第二天,小表哥朱家骝把我接到他工作的长途汽车运输队,在队长的安排下做临时工,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1.2元,把大块的焦炭敲成鸡蛋大小的碳球,简单、劳动强度不大,一起敲焦炭的不是半大小子,就是妇女。七八个人围在焦炭堆前,乒乒乓乓、说说笑笑一天过得真快。可惜只做了三天,汽车队为压缩开支,辞退了所有临时工。
刚有工作就失业,只好跟着姑母扛着把铁锹当零时汽车装卸工,那个工作就如同今日的散工,站在马路边等着需要装卸的司机叫,每部车只要六个人,而往往是数十人争抢着上汽车。爬上汽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先要眼观八路耳听四方,关注卡车的停靠和司机的叫声,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爬汽车,好在大家自觉,遵守不成文的约定,先上六人的随车工作,后上的下车等下一趟。姑母很灵活,每次她都能抢占先手,而且还要把我拉上车。卡车开到煤场是上煤,开到单位是卸煤,上煤坐空车安全,卸煤坐在煤堆上,飞驰着的汽车让人胆颤心惊。司机总像催命鬼一样“快快快”地厉声吆喝着。打煤过程中,不小心伤人很平常,姑母就上煤中就被旁边的小伙子铁锹划破了左鼻侧壁,一寸多长,鲜血直流,幸亏不深,闯祸的小伙子把姑母送进医院,清创包扎好伤口,付清挂号、诊治费,问姑母该怎么赔偿,姑母淡淡地说:“讨生活都不容易,算了,你今后做事千万小心点。”
除装卸汽车外,姑母带我到国营商店排队购买不要糕点票只用粮票的粗粮饼干,买回再高价卖出,这是政府打击的投机倒把行为,商店规定每人只能买一次,我在第二次排队时被商店工作人员认出抓住了,硬着头皮坚持说来自外地,卖点心为充饥,他们凶神恶煞地搜身,查无所获后,没收了仅有的半斤粮票和0.32元,最可惜的是他们也没收了马安植大哥留给我的纸条和附中的学生证。
春节前,姑母带着我到邮政局,填写一张十元的汇款单,一再嘱咐我写上“这是宗凡在合肥挣的钱”,填写完姑母要我给她念了一遍。
为让全家人能过好年,姑母独自爬汽车到合肥外八十余公里的东关乡下,找当地农民买干胡萝卜樱子,农民把收割胡萝卜果实后遗弃的叶茎收集晒干,留着没粮吃时充饥,胡萝卜樱很嫩很嫩时是兔子的最爱,没见过人当菜吃,长老了猪都不吃,现在成了救命的仙草。两天后,风尘仆仆的姑母得意地提着一小包干胡萝卜樱子回来,当晚用开水泡了一把,然后切得糜细糜细,和在大米中煮成饭,不管怎么捣碎、怎么煮,它始终如干草咬不动,怎么下去的还是怎么出来。1961年2月14日年三十,就是这种饭,让我吃饱了肚子。
春节后,姑母仍带着我打零工,舅舅四处求情托保,始终没能找到工作。2月下旬,我带着舅舅给我的路费,临别前,姑母用了家中的二斤面粉,烤成十六个面饼让我在路上吃,芜湖到武汉的船上水航行要整整两天,加上两边的火车,路上的耽误三天多才能到家,十六个面饼足够路上吃的,可我知道家里已多年没看见过小麦灰面了,一定得多留几个让大家尝尝,每天只吃二个饼,到汉口化0.1元、二两粮票吃了碗热干面,回到离开一个月的家同母亲姐弟共享面饼。
回长沙后,依然为寻找工作的事奔波发愁。
1961年4月,街道居委会介绍姐姐宗明到湖南大学桃子湖渔场当会计。介绍我到湖大总务处自行车修理店当学徒,每月工资十八元,报到时,我心里充满感激,立誓一定好好工作。修理店连我共三个人,二个师傅一个学徒。师傅是社会青年,做私活,用公家的零件修配自家的自行车,材料零件登记他俩人互打掩护,我用你证明,你用我证明,我很反感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认定他们不是正派工人。每天上班我最早到、最晚走,一人打扫店里的卫生,努力学习自行车修理的各种技能,工作的第十天,湖大总务处一位负责人来修理店修车,见我在为车轮正盘,随便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失学的原因,我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说了父亲的历史和我退学后的遭遇,听后他沉着脸一言未发走了。第二天上班,师傅通知我总务处辞退的决定,听此消息,我完全蒙了,一个极简单的、最下层的自行车修理工都要讲出身!与此同时,姐姐也被辞退了。
十六岁的我第一次感到惶恐绝望,是那么的无奈、那么的无助。
我拿着修理店里结算的5元工钱,拖着宛如千斤的双脚,一步一挪走到岳麓山下桃源村的山塘前,痴痴地望着静静的水面,呆呆地站着,泪流满面,站了好久好久……十四岁后再没人见过我流泪,实际上我多愁善感,泪泉特别丰富,只因是老大,打脱牙齿和血吞!泪流在人后,决不在人前!这就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
抬头问青天:一家人生存的希望在哪里?
我不敢面对风湿病瘫痪在床的母亲,病痛的折磨已使她奄奄一息,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被无情的阶级路线掐灭了。
要不是看见几个学生回家,我还会痴痴地站下去,最近拖板车、到合肥打工的所有经历一幕幕重放,绝望最终被肩头的责任击退。我抹干泪水,咬牙从5元钱里花0.64元钱,当然还用了粮票、糕点票,买回一斤桃酥,到家递給母亲,妈妈吃下二个桃酥竟奇迹般地来了精神,复苏了生气。后来的几十年中,母亲总说是几个桃酥把她从鬼门关里拖了回来,所以,我对桃酥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几十年来桃酥始终是我最喜爱的点心。
姐姐先到家,母亲知道姐姐被辞退,还残存一点希望,当我拿桃酥给母亲时,她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叫宗元和宗平吃桃酥,他俩说:这是妈妈治病的单方,任何人都不能吃!八岁多的弟弟都这么懂事,什么样的难关闯不过去呢?
母亲异常镇静,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天下之大,总有一条路是我们的!”
谁也没哭,谁也没说丧气的话,母亲的坚定使我信心倍增,“明天再去找工作!”这是我和姐姐的信念和决心。
一家人生死与共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