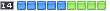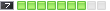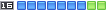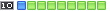无端的凌辱
1956年9月,小学六年一期,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劳累,时常让我想起母亲说“你舅舅十一岁就到中药铺当学徒”的事,我也有十一岁多了,到小学毕业时我过了十二岁,是能去当学徒的,我应付着完成六年级的学业,还是以优秀的成绩拿到小学毕业证书。1957年8月,去当学徒的想法占据我的头脑,在小升初的考试中,我的语文和数学的试卷都只做一半,落了榜,我很是自鸣得意,幻想自己长大了,成为工厂里的学徒了。
母亲闻讯气得嚎啕大哭,边哭边诉:
“不争气的东西,自暴自弃的东西!是要把我气死!刚刚十二岁,翅膀就硬了?好,你走,到社会上当二流子去,当我没生过你!”……
自从那次被母亲打手心,亲眼看见母亲伤心欲绝的哭泣,我特别害怕看到母亲的眼泪,母亲如此地伤心,我后悔了,连连发誓保证明年一定考进中学。
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辍学的一年中,也会尽力帮母亲做些事,或者去挣点小钱回来;有时守摊位,有时守在荣左路八字墙地段,等拖板车的运输工人叫去推车,八字墙的上岭全长约一公里,到长沙有色工业研究所止;那时的物资运输主要靠人力,搬运工人使用三米多长的人力胶轮平板车,一部板车每次承运一千多斤货物,搬运工人的劳动强度巨大,每次看见搬运工人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青筋突兀,搬运工人拖车到上坡前,会叫上一至二个小孩来推车,以减轻自己的重负。因此八字墙地段坡下总站着一群半大少年,因为我小,开始被喊的次数少,推了好几次车,搬运工人知道我推上岭时特别的卖力,我便成了这群半大小子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推一次上岭五分钱(0.05),每次出去总能挣回4、5角钱,把钱递到母亲手中,母亲眼眶红润,不说一句话。
1958年1月,连下了好几场雪,天气特别的冷,这些天因为下雪,我没去推板车,上午帮母亲看摊,让母亲在家休息,中午母亲替我回家吃饭,临走时母亲不忘嘱咐一句:“下午少玩点,读你六年级的书,记得你说过的话。”
腊月初八那天,连下了几天的雪,路上行人稀少,我九点出摊,十一点母亲来收摊。随母亲刚进家门,父亲原湖大商店的工友谭世宝尾随而来,他对母亲说:
“李妈妈,找你家老二问点事,一下子就回来。”
母亲笑呵呵地回答:“是谭师傅啊,进来坐吧。”
“不坐了,还是快去快回吧。”
“好,泉生去吧,莫贪玩,早点回来吃中饭。”
一路上谭世宝一言不发,我默默地跟着走进他家的厨房,灶台边站着他凶神恶煞的老婆,手里拿着个短扫帚,傍边站着她家的独生子“费伢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刚刚挨过教训的。“费伢子”比我小一岁,我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清楚他们找我究竟要问什么事。
“费伢子,你说,上午你都到过些什么地方?”谭妻瞟了我一眼,大声问。
“我先去了张婶的摊位,后来在李宗凡摊子旁讲了几句话,再没去过别的地方了。”费伢子低着头一字一句背书一样,没有停顿、没有节奏。
“李宗凡听到了吗?他只到过你那里,拿出来吧!”谭妻厉声问我。
“拿什么?”我一头的雾水。
“装什么蒜,三块钱,今天费伢子从家里拿走三块钱,要不是她张婶告诉我,我还不晓得他拿了钱呢。”
“我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呀。”我申辩了一句,转身想朝外走去。
谭妻用力抓住我手臂,恶狠狠地说:“想走?哪里走,交出三块钱你就走!”
“哎哟!”谭妻的力气很大,我痛得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委屈地说:“你莫冤枉人,我没拿费伢子的钱。”
“痛?你晓得怕痛啊!怕痛,就把三块钱交出来!”
谭世宝在旁帮腔说:“李伢子,拿了就拿出来,我们不告诉你妈妈就是。”
谭妻始终抓住我的手臂,我忍着痛,眼含泪,坚持否认拿了费伢子的钱。
谭氏夫妻轮番威逼,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你家最穷,只有你会偷。”“饥荒起盗心,肯定是你拿的。”“穷鬼见钱眼开。”“反革命的崽,是什么好东西!”……
谭妻几次举起手中扫帚,恫吓不交钱就要打人。
我眼中噙泪,一声不吭地任他们辱骂威逼,十二岁多的少年怎能抗御两个凶神恶煞壮年人的淫威,强忍着不让眼泪滴下来,低头死死盯着地面。
刚下班回家的龙伯伯看到这僵持的场景,忙问:“老谭,出了什么事?”
“李伢子偷了费伢子的三块钱。”
“宗凡,你到底拿没拿?”龙伯伯转头问我
“龙伯伯,我根本就冒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她们硬要冤枉我。”我的眼泪终于夹不住了,如断线的珍珠哗哗落下,哽咽着回答。
“老谭,大家都知道,李家的孩子个个品行好,一起打邻舍二年多,你又不是不了解,真的莫冤枉了人家孩子。”
谭妻恨恨地冲了龙伯伯一句:“说得轻巧,又没偷你家的钱,莫管闲事,反正他不交出三块钱,就别想回家。”
“莫以为有人帮你撑腰,就可以蒙混过关。”谭妻转脸,把手中的扫帚连连在灶台上拍打,说:“再不承认,不交出三元钱,这里是湖大的地盘,明天就不让你家在这里摆摊子了!看饿不死你们。”
龙伯伯见老谭夫妻油盐不进,就退了出去,见他出去,我心空了也怕了,摊位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了摊位,会……我不敢往下想了,喃喃说:“我回家找妈妈要钱给你,只要你让我家摆摊子。”
随着一阵冷风进来,门开了,母亲跟着龙伯伯急匆匆闯了进来,正听到我说的话,母亲正色问我:“你拿没拿钱,拿了就认,就深刻检讨,没拿就不该承认。人要有骨气,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低头。”
看见母亲,我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我根本就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他们骂我,把我的手臂抓得好痛,还说不准我们到这里摆摊子了,以后怎么办啊?”
母亲听完我的哭诉,气愤地问老谭夫妻:“你们说宗凡拿了费伢子的钱,你们看见了吗?有证据吗?”
“没亲眼看见,费伢子说拿钱后,到他那里后钱就不见了,不是他是谁!”谭妻说,语气没有了从的凶狠。
“没有证据你们就冤枉一个小孩,恐吓威逼,还抓伤了他!”母亲提高了声调:“走!去派出所,让警察来调查,是宗凡偷的,就赔,还要关他几天。”
谭妻应声说:“去就去。”
一直沉默的费伢子突然小声地说:“妈妈,莫去派出所吧。”
母亲看出了费伢子的胆怯,和颜悦色地问他:
“费伢子,你是诚实的孩子,好好想想,钱到底是在哪里不见的?”
费伢子迟疑了片刻,终于说出了实情:
“李妈妈,今天我偷了家里的三块钱,到过张婶和李宗凡那里,离开李宗凡时,我还从口袋里拿钱出来看过。后来,和同学一起完雪,堆了雪人后钱才不见的,我真不晓得丢在哪里了;我妈说是李宗凡偷了的钱。”
听完费伢子的陈述,母亲更气愤了,逼着谭氏夫妻去派出所,还要龙伯伯作证:“今天的事非去派出所不可,还我儿子清白!不能从小背个小偷的名声。”
谭世宝听完儿子的话,态度立转,低声道起歉来:
“李妈妈,真的对不起,错怪了宗凡,派出所就别去了吧。”
谭妻有些不甘心,丧气地咕哝着:“那我的钱不就白丢了。”
母亲听到这话,更是坚持要去派出所。母亲正告谭妻:“人穷也不是你能欺负的!本想看在邻居的份上算了的,你这样霸道,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吧,让警察来评判是非曲直,一还我儿子清白,二要检查我儿子手臂的伤情。”
老谭连连认错:“李妈妈、李妈妈,错怪了你家老二,我们不对,费伢子说钱在堆雪人后丢的,已经还了你儿子清白;我现在就带他去卫生科看手臂,是你谭嫂抓的,我认。她是文盲、没有知识,你大人大量,莫同她一般见识。”
龙伯伯也在傍调解,母亲心痛地仔细查看了我的手臂,然后抬头愤愤看看老谭夫妻,长叹一声,谢过龙伯伯,牵着我走出谭家。
回家后母亲对我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今往后你要挺直腰杆做人!记住,人的名声是一辈子的事,就是被打死也不能接受冤枉。”
这无端的屈辱,让我痛苦和愤恨了好多年,我恨强者的蛮横,我哭穷人的悲哀,更恨那些无知的成年人把淫威和羞辱强加给未成年的孩子。我拼命看《三国演义》、《水浒》、《三侠五义》等书籍,一心想成为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侠客,有一身的本领去抱打天下的不平,去惩治天下的恶人。
侠客没有做成,但自此事以后,我一生再没有屈服过淫威,一辈子挺直腰杆做人!为人行事敢作敢当,信守忠义,不凌弱小,不畏强暴!
还有件终身难忘的屈辱:
195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怀揣推板车得来的0.8元钱,兴冲冲赶到岳麓山下,想帮妈妈收摊早点回家。刚走到岳麓山邮政局前,看到一大堆人围着母亲的摊位,我从人群中挤到妈妈身边,只见一个身穿中山装衣冠楚楚的青年人,手里拿着件织好的毛衣和一小团毛线,指着母亲问:
“你贪污了我多少毛线?”
母亲一脸委屈,申辩道:“我用我的五个儿女发誓,没拿你一钱毛线。”
“没拿?我复了秤,少了一两多,我的毛线可是一块五一两的货啊。”
“取毛衣时我们当面过的秤,没有少呀,你在哪复的秤。”
“你管我在哪复的秤,反正是少了一两多毛线,你赔,赔我三元钱。”
“凭什么赔你,我没拿你的毛线。”母亲坚持着说。
“哼,能写会算,你究竟是什么人,不是个简单的家伙。”
“我是什么人?这里谁都知道,我是要养五个孩子的母亲。”
“哭穷?哭穷没有用,以为我会不要你赔钱,休想!拿钱来。”
他的毛衣用线一斤三两,手工钱收了三元二角五分,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织了四天,要是赔他3元,还剩多少?
母亲边哭边抗辩,那青年则越来越口无遮拦,语言尖刻恶毒且咄咄逼人,一边是二十多岁气势汹汹的年轻人,一边是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人群中终有人看懂了这场争吵的实质,一个中年人上前先问那青年:
“莫吵了,我问你是在哪杆秤上的复的秤?”
接着转脸再问母亲:“你收他的毛线又是用的哪杆秤的?”
母亲如梦方醒,连忙拿出桌子下我家的秤说:
“收毛线用的它,交毛衣时也是它。”
中年人接过秤,问青年:“是不是这杆秤?”青年人说“是”。
中年人从青年手中拿过毛衣和那剩余的一小团毛线,放进秤盘,边称边问:
“你交给大婶的毛线是多少斤两?”
“一斤五两。”
中年人仔细地看看秤杆的标尺,对青年说:
“没错呀!称起来一斤四两宏,一斤五两绵,都挂得住,除去几钱的损耗,你的毛线没有少呀。你是用哪杠秤复的?”
“我是在百货商店的小磅秤上称的。”青年说。
“磅秤上哪里能精确到几钱一两!没搞清楚就冤枉人,是你的不对了!”
事情清楚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指责起那青年来,有人叫“赔礼道歉”。
此时,母亲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说:“算了,不同你计较,你走吧。”
谁知那青年换了个话题,不依不饶地说:
“斤两的事就算是我说错了。但你的手工价格为什么要比别人贵?别人织毛衣都是二角钱一两,你却要二角五分钱一两,这是哄抬物价,是剥削!”
那种盛气、冷酷、蛮横和“大义凛然”的神态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母亲在河西的声誉很好,大多织毛衣的人,都是先来问母亲要卖多少毛线,然后买来毛线直接交给母亲,从不过秤,每次都是母亲一定要秤给他们看,他们在取毛衣的时候也从不复秤,拿着就要走,又是母亲秤好非要他们看,他们总是笑笑说:“李妈妈,莫看了,我还不相信你!”
那青年步步紧逼:“你退我六角五分钱就算了,不然我到政府那里告你。”
母亲忍无可忍了,她“抻”的站起身来,一把抢过青年夹在腋下的毛线衣,愤怒地吼叫:“我拆了它!退给你钱。”
青年被母亲的愤怒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母亲。
旁边的两个大姐上前一左一右扶着母亲,夺走母亲想要拆毁的毛衣说:“同他赌什么气,自己的劳动力莫糟蹋了,你为他打毛衣,他给你钱天经地义!”
人群中爆发出一边倒指责:“不像话,欺负一个残疾女人。”
“事先讲好价钱了的,年纪轻轻,太不讲理了吧。”
“没钱,你把毛线绕在身上吧,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没教养的家伙,替你爸爸脸红。”……
他知道犯了众怒,再也不吭声了,默默地接过大姐递给他的毛衣,低着头挤出人群,匆匆去了。
母亲替人织毛衣一直织到1964年,瘫痪在床上的几年里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无理取闹的事也就遇到这一次。
青年走了,人群散了,收了摊,母亲脸色铁青,看也不看我,独自走到自卑亭,不转弯走上回家的荣左路,径直走在牌楼口路上朝湘江走去,我心里有种不祥之感,害怕地紧紧跟在后面,抓紧母亲的衣角喊这:“妈妈回去吧!……”
母亲始终一言不发,走到河边站立在河堤上,望着滚滚的江水嚎啕大哭,我哭着、依旧紧紧抓住母亲的衣服,生怕手一松,母亲就会消失。
母亲这种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我一生只见过两次,1957年7月24日,我放学回家不见我家小摊,心中窃喜,以为母亲早收摊了,兴冲冲跑回家,母亲呆坐在床头,手扶着床柱默默流泪,见到我,突然恸哭,好久好久,母亲才抽噎着说:“你外婆七月二十号过世了,我不孝啊,让她为我担心了啊!”
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后,母亲在堤上坐了下来,抱着我说:“老二莫哭,放心,我不会跳河的,我死不得啊,我是个盆箍,我一死家就散了、你们就散了。”我央求着说:“妈妈,吓死我了,以后再莫到河边来好吗?”
母亲擦干眼泪,勉强地朝我一笑,坚定地答应:“好,再不来河边了!你考进师院附中的承诺,也要兑现啊。”
母亲说到做到,再没有一个人来到河边,即使是遇到天大的委屈和困难,她会独自徘徊到爱晚亭自叹自解,实在难出胸中闷气,就回家关上房门大哭一场,然后,擦干泪坚定地奔波在生命线上。
1958年8月,我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考进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