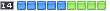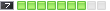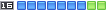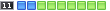艰难求生
1955年9月10日,父亲被捕三天后,湖南大学下达开除父亲公职的通知书,总务处派人结算父亲的工资,发放父亲九月份的工资,其中扣除父亲八月借支20元,将剩余的27元钱和工资清单一并交给了母亲,就此了断了父亲与湖南大学从1949年10月到1055年9月整整六年的工作关系。
现在,这27钱就是我家六口人生存的全部资产!
母亲哭过了,急过了,毅然抹去眼泪,拖着一条半残的腿,一瘸一拐奔走在教职员工的宿舍区和家属区,承接他们换洗的衣裤和被褥,来获取些许收入。当时洗涤的工钱价格是:里衣裤一件0.03元;罩衣裤一件0.05元;单人床单0.06元;双人床单0.1元;最贵被褥一床0,15元,因为被褥洗后要浆米汤。收来的脏衣物须记清楚人家,送错了和遗失都得由自己承担责任。
湖大的教职员工中有父亲一起教书、工作的老师和同事,所以常有好心人多找些衣物交给母亲,多给几分钱的工钱。湖大校区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不少,多为家庭主妇,当时男人的工资普遍偏低,有三个孩子的家厅,经济常捉襟见肘,健壮点的妇人就从事洗涤,挣钱贴补家用。收洗脏衣物的活不是天天有,母亲却从不走空,有几次母亲脚痛得厉害时,便让姐姐带着我去挨家收集脏衣物和送回干净衣裤。接回的衣物全靠手工搓洗,没有自来水,从前吃水是父亲从一里多外的井里担回来,现在就靠姐姐和我抬水了,洗衣用水更多,每天我和姐姐往返抬水几十趟,到收工时,我俩都累得瘫软了,母亲则更累,一天洗十几件衣裤,手泡得雪白没有了血色,从矮凳上起来还需我和姐姐一左一右搀扶。这样每天能收入七、八角钱,不然那仅有27元钱怎能支撑六口人的生存。
所以母亲说:“只要勤快,饿不死人的!”
邻居湖大工人龙伯伯,总是不声不响地挑满我家的水缸,每天洗衣洗被褥,用水量很大,而我家的水缸始终是满的。龙妈妈看见母亲得闲时,就会来家里劝慰、鼓励妈妈,她们的女儿七、八岁的龙淑媛,不像有的少年、儿童一样歧视我们,反而比过去更亲密。两家的友谊一直维系到1979年,我安家在河东,几个弟弟上山下乡了,不知不觉中疏断了往来。
1955年9月14日,姑母风尘勃勃的从千里之外的合肥赶到长沙,随身带来舅舅的信,舅舅在信中宽慰母亲,郑重承诺会尽其所能帮助我家。舅舅、姑妈(舅妈)一诺千金,他们资助我家整整十年,直到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三年后的1964年才停止寄钱给母亲。当时舅舅家里也不宽裕,他的月工资只有四十余元,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大表哥1953年辍学到安徽东关的一家工厂当学徒;家中还有外婆、表姐、小表哥和姑妈,日子同样过得挺艰难的。
姑母同母亲一见面,俩人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仍刺痛我的心!
姑妈止住泪说:“嫂嫂,莫哭了,我们一起商量以后怎么过吧!”
要独自抚养从二岁到十二岁的五个没成年子女,对一个身体健全的妇女讲也是极其沉重的担子,更何况是一个半残的中年妇女,那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担子啊,所有人都清楚其中的利害和艰巨,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朝代里都是少见而难以承受的重担啊。自父亲被捕后,许多好心人来劝母亲,也不乏幸灾乐祸的人出馊主意,无论是好心人还是幸灾乐祸的人,他们的共识是:无论如何要送走二个小儿子,留下大点的子女;不要读书去找事做。还有人送三个孩子,带二个孩子改嫁。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就是没有一个是自力更生、全家相守的意见。
母亲拒听一切意见,坚定地说:“儿子送人、改嫁,是万万不可能的,全家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处!而且书一定要读,就是讨米也要让孩子们读书!我会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还不能让他们成为无知无识的人!”
母亲的坚持招来些刻薄的讥议,那个在理发店前摆了个大摊位卖南食的女老板张胖子,敢于当着妈妈的面奚落说:“都这个时候还逞什么强,还守你的贞节牌坊,看你怎么守!非全饿死不可!”
背后的讥议就更多了,什么“不听劝,饿死活该”、“饭都冒得吃,还上学”、“还想考个状元出来,真是做白日梦”、“穷人富贵命,心强命不强”等等,难听的话不断传进母亲耳里,母亲一笑置之,不气也不恼,用那半残的身躯,硬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坚持让五个子女都上学。
母亲数次给我们讲述父亲年轻时求学的经历:
“你们的父亲,身揣一块银元,从零陵乡下独行千里到南京求学。乡下读的私塾,中文底子好,可对新学却是一窍不通,在南京举目无亲,同青年学子陈岩松合租个阁楼,奔波在南京各个中学校之间,找毕了业的高中学生,买回高中课本日夜苦读,每天以二个烧饼度日,没有了饭钱就去拉黄包车。他立誓要考进中央国立大学,报考中央国立大学首要条件是持有高中毕业文凭,他没有,巧遇一个叫李其坚的高中毕业生要回家继承家业。你父亲与他商量,用拖了半个多月黄包车的钱买下他的高中毕业证书,以此文凭报考。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央大学,完成了学业。‘李其坚’成他终生的名字。我不需要要你们挣钱,只要求你们安心、刻苦读书,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们深造下去的。”
后来母亲累倒了、瘫痪了,我和姐姐不得不离开学校寻找生计。我和姐姐便把读书的愿望全寄托在三个弟弟身上,他们个个争气,在学校都是品学双优的尖子生,完全能按部就班、轻松地上大学,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那个阶级斗争掌控一切的时代,书读得再好也是枉然啊!
大弟弟李宗元曾是长沙市的三好学生,成绩全年级第一,却没有资格上高中,1964年8月中考后,他的同学们都说:“李宗元,你要考不起高中,我们全班没有一个人能考起的!”阶级路线的威力显现了,全班就他落榜,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师大附中的一些学生抢出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宗元的档案上霍然盖着个长方形的大印:“此生不予录取。”命运就是这样让一个兰色小印章主宰着,时代和政策就是这样轻率地决定着人的一生。
1966年9、10月间,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净化城市、城市红色化等等群众运动中,顽强地抗御着居委会主任于荫球带领街道上的红五类民众,数十次上门逼迫下农村的挤压。11月,我随船从武汉回来,陪着刚松了一口气的母亲散步到岳麓山爱晚亭,在山下遇到子弟小学老师杨玉鹤,她详细询问了我家的状况,得知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而且是在“大中型国营企业”——(杨老师的话),很欣慰她教的五个孩子都健康长大了,依旧用温和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感伤地说:“你们总算苦过来了!就是太可惜,你们都是读书的种啊!
姑母在长沙的日子里,我整天粘着她,晚上同她睡在一个被筒里,从小我同姑妈最亲,在重庆和零陵乡下她带我的时间也最多,她常常取笑我:“你小时候就是个二呆子!别人要你的东西,想也不想全给人。”难怪我的父亲和母亲时不时打趣叫我二呆子。
劳动惯了的姑母接替了母亲洗衣服的工作,姑母做事又快又好,身心俱疲的母亲得到了短暂片刻的安宁和轻松。两个大人整天商量今后的生存方案,十天后作出了决定,姑妈带一个孩子去合肥生活,母亲在马路边支摊做点小生意。
听到这个决定我心里高兴极了,姑妈一直最喜欢我,肯定会带我去,到时我就能脱离这个屈辱的地方了,十岁多的我自然比几个弟弟想得要远些、深些,于是,只要在家,我是寸步不离开姑母,不时恳求姑母“带我去”。
母亲说:“宗亮随姑妈去合肥,他刚六岁,没上学,不要路费。泉生不能去,他正在上学,坐车要买票了,虽然是半票,到合肥也要花十元钱,有十元做本钱,我可以贩点花生、瓜子、糖果支摊了;泉生年龄大些,在家里还能帮帮我。”
姑母说:“带四毛去,嫂嫂放心,我会让他读书。以后我们按月寄十元钱来,你记住,你的身体垮不得,你一垮这个家就散了。”
当时的10元钱可以买近160大米(大米价0.06元一斤),能买回米,全家人就饿不死!我失望地接受了母亲和姑母的决定。
1955年10月18日,舅舅寄来30钱,姑母拿20做路费,留10元给母亲,第二天,在一家人生离悲伤的哭泣中送别了姑母和弟弟宗亮。
姑妈走后,母亲叫我和姐姐将家中一张长一米的小课桌,抬到岳麓山下上山的马路边,在邮政局前支起摊位,买回几个玻璃瓶装上糖果、花生、葵瓜子等,做起了小生意。本小利薄,每月利润仅仅只有十多元,每晚回家,母亲清点一天的收获,只要赚到了0.5元以上,母亲就会高兴地哼“木兰辞”,每当听到母亲的轻吟声,我会心定神怡、喜不自胜。我家支起的小木桌,与山路旁其他摊位的货架共处一地,显得那么的不合群和简陋难看。
坐摊时,母亲的双手从未停歇,一针一线替人编织着毛衣。母亲织工好,织出的毛衣均匀紧密、穿洗都不走样,名声很快传遍河西,上门的人日见增多,母亲更忙碌了,也更高兴了,每到深夜,我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母亲靠着床头织着毛衣,有时为赶工编织通宵。从1955年11月到1960年7月,一年四季酷暑严寒、室内屋外母亲的双手不停的上下翻飞,最终导致十指变形残废。
织毛衣的手工费按毛线斤两计算,岳麓区一带织毛衣的手工费有个不成文的统一的标准:每两0.2元工钱。母亲织了几件毛衣后,在一位好心学生的启发下,便自己定价每两收0.25元,一斤多毛线织一件毛衣,收入仅三元左右,母亲的工价比别人高出百分之二十,加工的毛线来源还是络绎不绝,日日赶工。母亲每月能织出六、七件毛线衣,收入稳定,每月的20元是我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姑母刚离开长沙,湖南大学总务处就来收房,来人说:
“房子已经分配给新来的商店经理。照顾了你们一个月,房租不收了,必须二天内腾出房子。经研究暂时安排你们搬到对面麓山馆7号带杂屋的房间,有个事得和你们说清楚,房间原是陈姓工友的住房,半个月前,他吊死在杂屋里,你们要是不怕,就搬进去住,要怕就另找房子搬家。家具只能搬一张大床和一张小桌子,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动。”
第二天,在龙伯伯和金明爸爸等人的帮助下,一家人搬进了这间刚死人不久的凶宅。搬进去时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窃窃私语:“还有真不怕鬼的”、“吊颈鬼最凶了”、“这房子闹鬼,哪里能住人啊”、“她家男人是大特务,不会怕鬼”、“可怜,是没办法呀”……好话歹话说什么的都有。
顿时我心底涌出一阵恐惧,抬头看母亲,她对一切闲话置若罔闻,有条不紊地整理着我家少得可怜的物品。接触到母亲坚定无畏的眼神,我的心平静了,同妈妈在一起,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大,弟弟们小,我应该做榜样。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十岁少年心中产生的恐惧,为何会在一瞬间消失,想来想去都没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就把它归结于天生胆大不信鬼。
麓山馆7号是个深宅大院,属官僚资产,收归国有后成为湖大职员工友的住宅。宅院坐西朝东,三丈高的围墙圈住宅院,气派宽敞的大门朝东,正对着湖南大学办公楼,后门朝西出门就踏上上岳麓山的大道,南边有个侧门,通向湖大学生宿舍和灯光球场。大宅院里如迷宫一样,九曲十八弯住着数十户人家,它在上世纪末已灰飞烟灭,里面到底有多少间房、住了多少户人家至今我都没搞清楚过。
家安好了,出于对新环境的好奇,我带着弟弟满大宅院里游走,两次迷路,两次是宅院里的大人送我们回家。母亲两次都说:“不要太好奇,不要麻烦人,总让人送,惹人烦的,你们三兄弟少出去些,就在家里玩吧。”母亲的确怕麻烦人,而更怕是我们在外面遭到歧视和侮辱。
此后,我就不再带弟弟到走进宅院深处了,龟缩是在自家屋里或者出后门在熟悉的马路边玩耍;我和宗元最喜欢捉弄小弟弟,常跑进那间吊死人的杂屋里,叫小弟宗平来抓我们,总要等到宗平在门外大喊大叫,哇哇大哭才出来,母亲回来以告状,免不了一番责怪,我们呢,第二天依然故我。
我家四个小孩,一女三男,个个乖巧听话,一身的补丁衣裤,却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放学回来三兄弟翻新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没多久便引起麓山馆7号宅院里大人和小孩的关注,聚拢在我们身边玩耍的儿童渐渐多起来,家长们也放心自己的儿子同我们一起,我成了孩子头,常带着十几个孩子“打游击”。
三岁的小弟弟宗平,性情温和好客,我们上学后,他带着一般大小的孩童,学着我的样子充起了孩子头,他聚众树立威信的方法简单直接,趁母亲到河东进货的机会,将自家待出售和赖以生存的货物——糖果分发给每个小朋友,母亲回家,近10元的糖果全进了孩童们的嘴里。母亲没说什么,但二天后,这些孩子的家长知道后,这个一元、那个二元,将钱塞到母亲手中,收回的钱是买回这罐糖果的一倍。母亲感激地对我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正是母亲无数次的念叨“世上好人多”,影响着我,“不设防”相信人追随我一生。
是啊,我何尝没遇到过好人,记得一个陌生的青年学生把我叫到僻静处,问:“你是李其坚先生的儿子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掏出五元钱装进我上衣口袋,说:“回去给你妈妈。”没留姓名转身走了,留下我一生无处答谢的感激。
老天爷保佑,我们住进凶宅,一直清吉平安,大人小孩从不生病,活泼健康,生龙活虎,而且,过去的凶宅如今成了众多孩子来得最勤的地方。
我不怕鬼,世上没有鬼的信念,就是在这里养成的。
鬼是从来没有欺负和恐吓过我们,倒是隔壁的两个大活人,总是不断地骚扰着我们的生活。我家住房的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五十多岁,她们天生厌恶反感孩子的嬉笑声,白天,我们的笑声稍大点,他们会“砰、砰、砰……”用力拍打木板做的间墙,木墙上的粉灰顿时落得满床都是;天黑,家里不能传出大声话音,更不能有笑声,她们一旦听到,会歇斯底里地锤着木板墙,高声怒骂,一直骂到她们精疲力竭方休;为避免他们的辱骂,我们兄弟白天不再在屋里玩游戏,晚上也不敢笑,说话总是细声细气,尤恐声音传过木墙惹来咒骂。平日,那老太太每次看见我们,总用斜乜奇特的怪异眼神死死盯着我们好久好久,看得我心毛骨悚然,我会牵着弟弟立马落荒而逃。直到成年后,我才知道那种眼神是聚嫉妒和羡慕、刻毒和矛盾于一体的产物。
一天放学回家,大弟弟宗元神秘地告诉我,邮政局里来了个酷似父亲的人,我立刻随他跑到邮政局,立在大门外观望,那个人几乎与父亲一模一样,我差一点冲口喊出“爸爸”,一段时间里,偷看“他”,是我思念父亲最好的慰藉。
三个月后,父亲的判决书下来了,判决书上称: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尘埃落定,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分子的崽,从此,最怕被人骂“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崽。”为逃避这句话,我宁可吃亏也不抗争。后来想想,这样反使我交到许多维持几十年友谊的朋友,也算是逆境给我的另种收获吧。
经不住隔壁那对老夫妻的多次反映,兼之湖大总务处管房子的人换了,我家已不再是湖大家属,没有权利住湖大的房子。这间凶宅经我家住后,没出现任何闹鬼现象,而且孩子们个个健康,收回来完全有理由说服其他职工来居住了。
于是,湖大总务处再次下达三天搬家腾房的驱逐令。 |